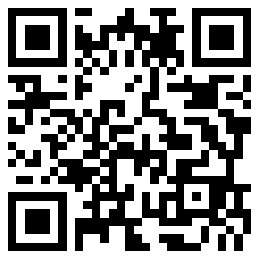核心提示
过了“中立交”,一拐弯就到樊沟了。由于挨着铁路,新中国成立前后,樊沟村民多是下苦力的铁路搬运工。樊沟很大,居民分散在樊沟街、向阳巷、光明一巷、延安路樊沟新村4个片区。樊沟很有趣,旧时村南有条“十里长沟”;村西小吴庄有打鸡蛋村之称,蛋清、蛋黄分开卖……10月26日,记者来到铁西的樊沟社区,探访出许多“老许昌”都不知道的樊沟旧事。
樊姓人居住地有长沟,故名樊沟
在记者的印象中,樊沟距离老城很近,过了“中立交”一拐弯就到。但10月26日,记者驱车来到延安路与许继大道交叉口东北角,才找到樊沟社区居委会。居委会后面是樊沟新村。
“樊沟社区居委会咋‘怼’到了延安路上了?这里也是樊沟?”记者有些不解。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们樊沟社区大着呢。” 樊沟社区党支部书记安国明笑着说,“老许昌”印象中的樊沟,可能仅仅局限在铁路西侧的樊沟街。其实,原来樊沟面积很大,从解放路至延安路都有土地,现在虽然土地没了,但樊沟居民依然分散在樊沟街、向阳巷、光明一巷、延安路樊沟新村4个片区。“因此,樊沟社区居委会建在延安路上也不奇怪。”
为了更好地挖掘樊沟历史,记录铁西城市发展,安国明特意邀请了5名社区老人一起座谈。他们分别是85岁的常桂枝、81岁的菅秀菊、77岁的李丙照、80岁的王荣彬和81岁的吴海全。他们中有樊沟生产队队长、民兵营长、老厂长和技术骨干,见证了樊沟的艰辛发展历程。
说起樊沟的由来,几名老同志不由地打开了话匣子。
“樊沟,顾名思义,就是姓樊的居住地附近有条沟。”李丙照说,樊沟原来叫村,2003年村改居。村中有樊、安、郭、吴四大姓,樊姓人最多,占了一半。老村庄在铁西的运粮河西岸,现在的许继大道东风桥的西南角。他小的时候,村南头有条长长的深沟。“我个子算高的了,跳进去都不露头。”
“再高的人跳进去也不会露头,我印象中这条沟有3米深。”王荣彬接过话茬说,该沟东起运粮河,沿着如今的光明路一直向西,在五一路与光明路交叉口向西南延伸,将碾上括在里面。“千年的大路压成沟。以前村里的老年人说,这条沟曾是许昌通往南阳的官道,废弃之后变成了一条沟。很早以前,该沟长10里。”
吴家人在此守坟,衍生三个小吴庄
81岁的吴海全说,樊沟原来和碾上是一个生产大队,1961年才分离出来。樊沟大队有樊沟和小吴庄两个村。两个村庄都不大。20世纪50年代,樊沟村有200多口人,小吴庄有80多口人。“别看小吴庄人不多,但人口较分散,内部又分成3个小吴庄。3个小吴庄分别位于现在的延安路老法院东、光明剧场和许富花园小区一带。”
小吴庄居民是吴家坟守陵人的后代。吴海全介绍,吴家曾出高官,为帝王师,死后葬于城西,坟冢高大,松柏森森。“吴家坟占地百十亩,位置在现在的光明小区一带,坟地里坟茔众多,人进去看不到头,白天小孩儿都不敢进。”吴海全回忆道,后来铁西兴建工业区,吴家坟被逐一平掉,20世纪80年代左右消失。
老法院东侧的小吴庄曾有打鸡蛋庄之称。对于名称的由来,几名老人的说法不一。有的说,村民精明有头脑,卖鸡蛋时蛋清、蛋黄分开卖,人送村名打鸡蛋村。但吴海全不这么认为。他说,民国时期,许昌城中开了一家蛋厂,村民进厂打工,主要工作就是将鸡蛋打开,分离蛋清和蛋黄。下班时,村民将成筐的蛋壳拿回家碾碎当肥料。因此,这个小吴庄又被称为打鸡蛋庄。
说起蛋厂,李丙照突然想起来了什么。他说,有一年,他在村中烟炕听到4个老头儿聊天儿,说城中有个元丰蛋厂,打鸡蛋庄的人就在那里干活儿。该蛋厂还在打鸡蛋庄设了一个收蛋点。“打鸡蛋庄在许南官道旁,路边有一个施茶庵,供过往路人免费喝茶。”
记者查阅1993年出版的《许昌县志》得知:“1915年,浙商阮规方在许昌开设元丰蛋厂,将蛋清、蛋黄加工外运,日加工鸡蛋65万个。后又有豫昌蛋厂、福义蛋厂相继开设。1937年日军侵华,各蛋厂先后歇业。”因此,打鸡蛋庄之说并非空穴来风。
樊、安、郭、吴四姓人是老户,其他都是外来户
樊沟在许昌老城西郊,村东南有运粮河环绕。进城时,樊沟桥是必经之路。“桥面不宽,又称小桥。推着架子车过桥时,稍不注意,车轮就会陷进青石板缝隙中。”81岁的菅秀菊是樊沟的媳妇,回想起年轻时推着小车过小桥的经历,感慨万千。“这座小桥没有栏杆,桥面上的石板被车轮碾压得缝隙很大,一旦车轮卡在石板中,车辆动弹不得,十分尴尬。因此,妇女们推车从那里走时很害怕。”
现在的樊沟桥比老桥宽了许多,能通行两辆小汽车,但桥的长度锐减,只有10米左右。85岁的常桂枝说:“老樊沟桥比现在的樊沟桥更靠东。以前的运粮河水面较宽,樊沟桥东西长百十米。”
由于离城比较近,在民国时期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樊沟居民经常“跑警报”。“城里的警报一响,村民就往西面跑。有的躲到地窖里,有的趴在庄稼地中,等到飞机飞走后才敢出来。”当年“跑警报”的经历给李丙照留下了心理阴影。有一年,城中响起警报声,四五岁的他赶紧往地窖方向跑,慌乱中不慎跌倒。这时,其身后响起机枪扫射声,地上冒出一道白线。“再晚一步,就扫到我身上了……”
樊沟的樊、安、郭、吴四大姓是老户,祖祖辈辈在樊沟居住。樊沟的其他姓氏均是后来搬迁而来的。
“我们王姓是樊沟第一个外来户,这还得从我的爷爷说起。”王荣彬说,他的爷爷是巩义人,年轻时闯荡开封,后来到了许昌。“我爷爷为人豪爽仗义,在许昌结交了一众好兄弟。用许昌话说,我爷爷在许昌混得很开,曾是许昌四大绅士的座上宾。”
“后来,我的爷爷当了许昌脚行的把头,许昌火车站的搬运工都归他管。”王荣彬说,民国时期,脚行人员三教九流,有破产的农民、无业的市民、小商贩、土匪、黑帮成员。许昌解放后,搬运行业同样鱼龙混杂,各种人群混迹其中,管理难度很大。他的爷爷当上脚行的把头,足以说明其江湖地位。
有了王荣彬爷爷的这层关系,民国时期的樊沟人多从事搬运工作。搬运工作虽然辛苦,但收入相对稳定,为家庭增加了收入,改善了拮据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