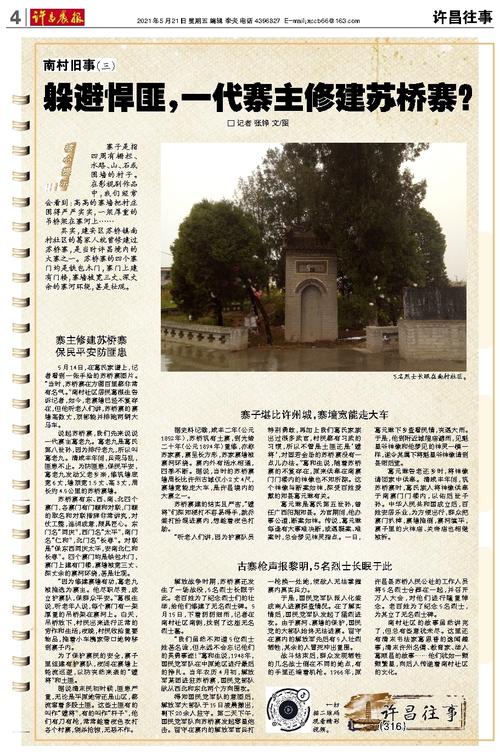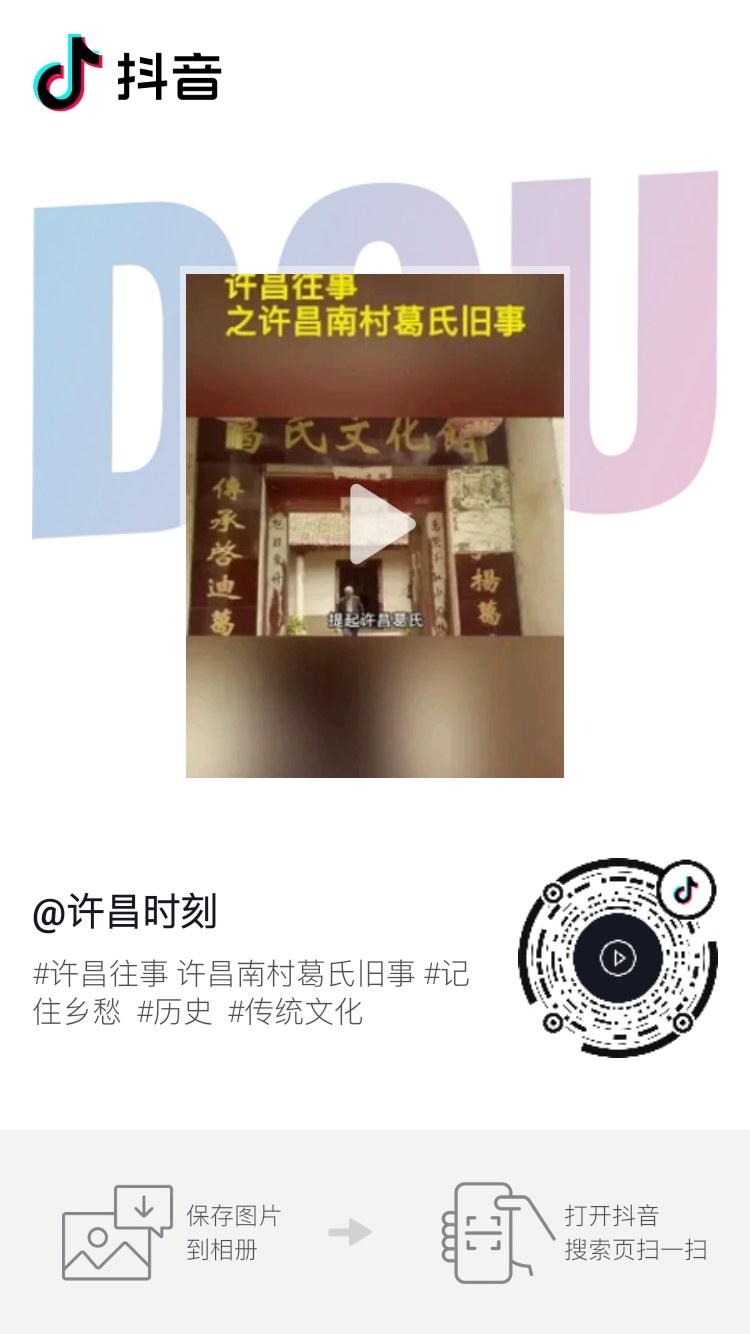□ 记者 张铮 文/图
核心提示
寨子是指四周有栅栏、水路、山、石或围墙的村子。在影视剧作品中,我们经常会看到:高高的寨墙把村庄围得严严实实,一架厚重的吊桥架在寨河上……
其实,建安区苏桥镇南村社区的葛家人就曾修建过苏桥寨,是当时许昌境内的大寨之一。苏桥寨的四个寨门均是铁包木门,寨门上建有门楼,寨墙被宽三丈、深丈余的寨河环绕,甚是壮观。
寨主修建苏桥寨 保民平安防匪患
5月14日,在葛氏家谱上,记者看到一张手绘的苏桥寨图片。“当时,苏桥寨在方圆百里都非常有名气。”南村社区居民葛根生告诉记者,如今,老寨墙已经不复存在,但他听老人们讲,苏桥寨的寨墙高数丈,顶部能并排跑两辆大马车。
说起苏桥寨,我们先来说说一代寨主葛老九。葛老九是葛氏第八世孙,因为排行老九,所以叫葛老九。清咸丰年间,兵荒马乱,匪患不止。为防匪患,保民平安,葛老九发动父老乡亲,修筑墙底宽6丈,墙顶宽1.5丈、高3丈,周长约4.5公里的苏桥寨墙。
苏桥寨有东、西、南、北四个寨门,各寨门有门额和对联,门额的取名和对联措辞非常讲究,对仗工整,连词成意,颇具匠心。东门名“同庆”,西门名“太平”,南门名“仁和”,北门名“长春”。对联是“保东西同庆太平,安南北仁和长春”。四个寨门均是铁包木门,寨门上建有门楼,寨墙被宽三丈、深丈余的寨河环绕,甚是壮观。
“因为修建寨墙有功,葛老九被推选为寨主。他尽职尽责,成立护寨队,保群众平安。”葛根生说,听老年人说,每个寨门有一架厚重的吊桥架在寨河上。白天,吊桥放下,村民出来进行正常的劳作和生活;夜晚,村民收拾重要物品,推着小车携家带口地转移到寨子内。
为了保护寨民的安全,寨子里组建有护寨队,夜间在寨墙上轮流巡逻,以防突然来袭的“蹚将”和土匪。
据说清末民初时候,匪患严重,无论是平原地带还是山区,都流窜着多股土匪。这些土匪有的叫作“蹚将”,有的叫作“杆子”,他们有刀有枪,常常趁着夜色攻打各个村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寨子堪比许州城,寨墙宽能走大车
据史料记载,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苏桥筑有土寨,到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重修,亦称苏家寨,寨呈长方形,苏家寨墙被寨河环绕。寨内外有活水相通,四季不断。据说,当时的苏桥寨墙周长比许州古城仅小2丈4尺,寨墙宽能走大车,是许昌境内的大寨之一。
苏桥寨建的结实且严密,“蹚将”们深知硬打不容易得手,就乔装打扮混进寨内,想趁着夜色打劫。
“听老人们讲,因为护寨队员特别勇敢,再加上我们葛氏家族出过很多武官,村民都有习武的习惯,所以不管是土匪还是‘蹚将’,对固若金汤的苏桥寨没有一点儿办法。”葛和生说,随着苏桥寨的不复存在,原来供奉在南寨门门楼内的神像也不知所踪。这个神像与断案如神,深受百姓爱戴的知县葛元琳有关。
葛元琳是葛氏第五世孙,曾任广西阳翔知县。为官期间,他办事公道,断案如神。传说,葛元琳每逢有大事难决断,或遇疑案、难案时,总会梦见神灵指点。一日,葛元琳下乡查看民情,突遇大雨。于是,他到附近城隍庙避雨,见魁星爷神像和他梦见的神灵一模一样,遂令其属下将魁星爷神像请到县衙后堂。
葛元琳告老还乡时,将神像请回家中供奉。清咸丰年间,筑苏桥寨时,葛氏族人将神像供奉于南寨门门楼内,以佑后世子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姓安居乐业,为方便出行,群众把寨门扒掉,寨墙推倒,寨河填平,寨子里的火神庙、关帝庙也相继被拆。
古寨枪声报黎明,5名烈士长眠于此
解放战争时期,苏桥寨还发生了一场战役,5名烈士长眠于此。老百姓为了纪念烈士们的壮举,给他们修建了无名烈士碑。5月15日,下着沥沥细雨,记者在南村社区南侧,找到了这座无名烈士墓。
“我们虽然不知道5位烈士姓甚名谁,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英勇事迹!”葛和生说,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中原地区进行最后的挣扎。当年农历4月初,解放军某团进驻苏桥寨,国民党部队欲从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围攻。
得知国民党军队的意图后,解放军大部队于15日凌晨撤出,剩下20余人驻守。第二天下午,国民党军队向苏桥寨发起零星炮击。留守在寨内的解放军官兵打一枪换一处地,使敌人无法掌握寨内真实兵力。
于是,国民党军队派人化装成商人进寨探查情况。在了解实情后,国民党军队发起了猛烈进攻。由于寨河、寨墙的保护,国民党的大部队始终无法进寨。留守在寨内的解放军先后有5人壮烈牺牲,其余的人冒死冲出重围。
战斗结束后,群众发现牺牲的几名战士倒在不同的地点,有的手里还端着机枪。1966年,原许昌县苏桥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将5名烈士合葬在一起,并召开万人大会,对他们进行隆重悼念。老百姓为了纪念5名烈士,为其立了无名烈士碑。
南村社区的故事虽然讲完了,但总有些意犹未尽。这里还有清末书法家葛恩普的逸闻趣事;清末许州名儒、教育家、举人葛顺昌的故事……他们犹如一颗颗繁星,向后人传递着南村社区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