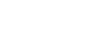拂晓,老钟起床,腰里塞着短斧,悄悄摸上野马岭,藏在一块大石后查看。野马岭上血迹斑斑,可见昨夜双方交火之惨烈。老钟仔细察看,没发现游击队的踪迹。很显然,战场被清理过。老钟暗自懊悔,自己来晚了。
昨天夜半,密集的枪声忽然响起。老钟从睡梦中惊醒,侧耳静听,像是从野马岭传来的。没多久,枪声渐稀。零星的几声枪响后,深夜又陷入了死寂。
下山的路上,老钟想起一处隐秘的山洞,便摸了进去。
山洞里的人已经奄奄一息。老钟认识,是游击队的李队长。老钟的儿子也在游击队。李队长用尽最后的气力,交给老钟一个绣着荷叶的烟荷包,并用微弱的声音让他去镇上的裁缝铺,接头暗语是:“今晚有出远门的大船吗?”答:“有。渡船上是新修的桅杆!”暗号对上了,就把这个烟荷包交给对方。
“要是……裁缝铺……有敌人,就去找疯,疯……”
“风什么,李队长,风什么?”然而,无论老钟怎么呼喊,李队长再也没有任何声息了。
老钟紧紧攥着烟荷包,抹着眼泪下了山。离开前,他用短斧砍来许多枝条,把遗体掩盖,三鞠躬后说:“李队长,对不起了,以后再给您修墓立碑。”
老钟回家换了衣服,乘渡船来到镇上。镇上倒显得平静,除了“鬼子”“二鬼子”在正常巡逻,就是为数不多的乡亲在购买急需的日用品。一个不知哪里来的疯婆子,拄着竹竿,端着豁碗,笃笃笃在前面走,边走边对路人说,可怜可怜我吧!给点儿吃的吧!
老钟警惕地躲在暗处,仔细地观察裁缝铺许久。他觉得没什么异样,又摸了摸腰间的烟荷包,这才决定前去接头。他压低头上的斗笠,若无其事地踩着石板路,低头向裁缝铺走去。
快到裁缝铺时,一阵吵嚷声传来。
“疯婆子,找死啊!快滚,滚远点儿!”随着一声呵斥,只见两个衣着体面的人,推推搡搡地把疯婆子从裁缝铺轰了出来。疯婆子跌倒,手里的竹竿和豁碗摔在地上,在青石板上滚出老远。
老钟心知有变,赶忙上前替疯婆子捡起竹竿,又把滚落的豁碗追回来。疯婆子唠唠叨叨,对着那俩人骂个没完。看到疯婆子,老钟想起了自己的老母亲。他把豁碗递过去说:“老人家,您在哪里安歇,俺送您过去?”
疯婆子夺过豁碗,突然一把攥住老钟的手腕。老钟一惊,看起来瘦弱的疯婆子竟是很有力气。疯婆子目光一凛,迅疾低声道:“别说话,跟我走!”
出了镇子,确定安全无虞后,疯婆子才指指老钟腰间的烟荷包,举起竹竿作威胁状,厉声道:“说,哪里来的?”见老钟慌乱,又压低声道:“今晚,有出远门的大船吗?”
老钟恍悟,回道:“有。渡船上是新修的桅杆!”
李队长的遗言里,万一裁缝铺有变,应该是要他找这个疯婆子。老钟镇定下来后,将烟荷包从腰间解下,郑重交到疯婆子手里。
“李队长呢?”疯婆子急切地问,“他怎么样了?”
老钟望着远处的渡口:“他,牺牲了。”疯婆子无言,艰难地哽咽了一声,转身踉跄走远。
第二年,抗战胜利,镇上插遍了红旗。渡口的老船工年事已高,老钟接替他撑起了渡船。大军南下的时候,老钟和乡亲们摇着撸,送走了一船又一船的解放军战士。看着这些朝气蓬勃的面孔,老钟想起牺牲在前线的儿子,禁不住热泪盈眶。
夜来大雨,湍急的河水迈着铿锵的步伐奔向远方。
晨光给天际抹上一把红晕,哗哗的流水声里,老钟蹲在船尾,给病中的老母亲熬中药。急剧的咳嗽声不时从船舱里传出来,老钟听得心惊肉跳。老母亲病势严重,总不见好,老钟隐隐有些担心。
“船家,过河吗?”岸上忽听有人喊。
老钟抬头,眯起眼,隔着稀薄的河雾打量。来人穿着军装,女的,有些面熟。
女人微笑道:“大哥,可找到您了。怎么了,不认识了?”见老钟沉吟不语,女人又说:“我是李队长的爱人。解放了,想接老李回去……今晚,有出远门的大船吗?”
女人说着,用力抹了抹脸上的泪。
老钟忽然泣不成声。他极力按捺起伏的情绪,站起身高声回答道:“有,有啊!渡船上是……新修的桅杆!”这句话,老钟在睡梦中已经自问自答不知多少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