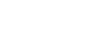1963年10月,妈妈去世几个月后,在许昌农村住的姥爷心疼我爸爸领着几个不满10岁的孩子太艰辛,就发电报让我爸爸把几个孩子带到许昌,去他家过日子,彼此也有个照应。就这样,我们和爸爸一起在许昌定居了下来。从老家出发之前,我要爸爸把妈妈用来养活我们兄妹几人的破竹篮和圆筒玻璃瓶带到许昌,用绳子将它们在屋梁上,这样,一见到此物,妈妈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我们眼前。睹物思人,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兄妹几人还深深地怀念着母亲。
1957年春天,那时妈妈还在。听妈妈说,爸爸从小在外当兵,没学手艺,在小县城里连个谋生的手段都没有。好在爸爸有几个发小,经商量,他们几个去给人做挑夫。爸爸挣的钱除了自己糊口外,所剩无几。
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那时刚刚9岁,一个妹妹年仅5岁,还有一个弟弟不到两岁。妈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她千方百计出去找活儿干。经人介绍,她找了一个圆筒形的玻璃瓶,在小卖部以低廉的价格批发了一瓶雪花膏,装在一个破竹篮里游乡叫卖,或以物易物,换点儿能充饥的东西。那时的雪花膏在偏远的山乡里被视为稀罕物,大姑娘、小媳妇抢着要。
记得一个乍暖还寒的黄昏,天色已晚,妈妈还未回来,我很担心,就牵着妹妹、抱着弟弟,饥肠辘辘地站在江边等妈妈。我仨站在岸边,眼巴巴地望着江对面,盼着妈妈早点儿出现。妹妹稍大一点儿,比较听话;弟弟不懂事,饿得哇哇哭,哄都哄不住。我也饿了,见不到妈妈,忍不住也想哭!放眼望去,只见灰蒙蒙的江水缓缓向东南流去。猛一下,我隐约瞅见对岸一个身影踏上了渡船,似乎是妈妈。我心里一喜,对弟弟和妹妹说,上船的那个人好像是妈妈。随着渡船慢慢靠岸,我们看清了,那就是妈妈。我们情不自禁地连声高喊:“妈!”说话之间,船靠了岸,妈妈跨上来,妹妹不顾一切地扑向她,抱着妈妈的双腿不松手。妈妈把篮子放在一边,连声说:“乖,饿了吧?今天卖的雪花膏多,回来晚了!”我也走向妈妈,扶着她的肩膀,感慨地说:“妈,累坏了吧?”我接过篮子,只见玻璃瓶里的雪花膏已经见底了,篮子里有半篮小小的薯头和一些小小的红薯干。妈妈说:“走吧,孩子们,回家妈给你们煮红薯吃。”妈妈抱着弟弟,妹妹懂事地拉着妈妈的衣角,我们披着夜色匆匆朝家走去。
1963年,妈妈因长期劳累,不幸患了急性心脏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那一年,我的妈妈还不到60岁。
妈妈去世后,爸爸一个人承担起照顾我们兄妹三人的重担。他没有别的谋生本领,仍然在外给人做挑夫。他一方面下着苦力,一方面还得照顾我们兄妹三人,忙里忙外,顾住这头顾不住那头,真够难为他的。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该为老爸分忧了。我负责照顾弟弟和妹妹,慢慢地学会了做饭。
记得有一次,爸爸挑着空担回家了,他摘下肩垫脱了衣服休息,我看到他的双肩被扁担磨得发红、发紫,几乎渗出血来,左肩上还被压得起了一个大红包。我不由得鼻子一酸,流下了眼泪。我心疼地问他:“爸,肩膀痛不痛?”爸爸说:“没事,我不痛。”
后来,姥娘,姥爷相继去世,在舅父、舅妈的照顾和左邻右舍的帮助下,我上了小学、考上了初中,随后又考上了高中。后来,我成为一名教师,直到2008年才从教师岗位上退休。
2019年9月,我70多岁时,患前列腺癌住院治疗,因手术不太成功,落下尿频、尿急等后遗症。
刚出院时,我每天要换好几个成人纸尿裤。后遵医嘱,经过物理调理和中药治疗,我现在基本上康复了。
我禁不住想起当年70多岁的爸爸。那时,他也有前列腺方面的毛病,而我们并不知情。母亲去世得早,爸爸又当爹又当妈,无人贴身照顾他。
这种病,夏天还好一点儿,裤子湿了,随风一风,或到无人的角落里把裤子脱掉,拿在太阳下晒一晒,一会儿就干了。可到冬天,爸爸就遭罪了。
那时家里穷,我的两个儿子在城里上高中、一个女儿在上初中,我的工资又低,爸爸深知家中的困境,即使自己受点儿罪也不开口让我给他看病。妹妹远嫁他乡,弟弟是个农民,所以照顾爸爸的责任就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在中学教学,学校要求教师吃住在校,我经常不在家。妻子既要种地,又要操持家务,她对我爸爸的身体状况也不知情。
记得有一年放寒假,我回到家里。经常和我爸爸相处的乡亲责备我说:“你爸爸的裤裆都成啥样了,你们也不管管?”回到家,我才发现,天寒地冻,爸爸没有替换的棉裤,滴湿的裤裆冻成了冰疙瘩,用手一敲,硬邦邦的。此情此景,让我无地自容。
我们夫妻俩在集市上给爸爸买了两套新衣服,又领他到市里最好的医院治病,爸爸的病基本上治好了。
每每想起爸爸在世时遭的罪,我就心疼。我亲爱的爸爸、妈妈,我永远爱你们,永远怀念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