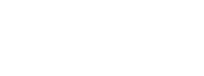端午小长假前夕,打电话到家里。
电话是父亲接起来的,“谁呀?”声音还是那样的粗犷,听不出一丝客气。
听到是我的声音,父亲就聊几句,无非是让我注意身体,减减肥,别回来一次胖一圈儿。
随后父亲便把手机转给了母亲,嘴里说着“你儿子的电话”。
这样的套路和语气,基本上都和上次一样,甚至连通话时间都不会差多少。
有时候,我常常有种错觉,我们不是父子,父亲只是一个天然的接话员,抑或是一个传话筒,在母亲无暇理会时,可以替补一下,仅此而已。
我能想象得到,此时的父亲多半是坐在灶台前烧火,下他爱吃的捞面条。母亲应该是在院子里,或者厨房里忙碌着,收拾着东西。
听到父亲的话,她多半会说,“又打电话干啥,净是浪费钱”。但电话她还是接了过去,而且会去住的里间屋子,可以安静地和儿子聊上一会儿。
母亲出生在一个农村干部家庭,曾经也是戴着上海牌手表、骑着凤凰牌自行车去上卫校的“傲气女孩”,但她没有一丝大小姐脾气,从小都是把钱掰成两半花。
从家里有手机开始,手机里的话费从来没有超过30元。每次我回家,都要帮她删去手机里那说不清有多少条的短信,提醒她要交费了。但母亲从来不去交费,还理直气壮地反驳我:“里面还有3块多钱,我又不打,只是接接,足够了。”
似乎有点偏题了,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家里小麦是不是快要收了,照理儿,这时候差不多了。
母亲说:“还要等几天呢,端午节是不行,东地麦子还青着呢,也倒了,到时候不是太好收。南地还好,没有事,到时候直接下地收就行。你不用操心了,让你扛粮食袋子,还不如你爸,个子怪高。人家金仨还没你高,一个胳膊夹一袋粮食站起来就走,就这你还不锻炼。”
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就很汗颜。
确实是,收麦在以前可是个力气活儿,现在也是,不过要省事很多了。
记得那时,每当收麦前一两周就要轧出来一个场面,平平的,上面可以打场,可以晒粮食,这也是收麦前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了。
轧好的场面,就是收麦的后勤保障基地,也是仓库。四轮车、拖斗、石磙、大水缸、木板床……只要是你能想到的、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农机具,在这里应该都能找到。水缸是每个场面里必备的,更有乡、村干部来检查,因为那是用来防火的。那时候的我,最喜欢的就是趴在水缸那里玩水,或者从水塘里逮几只青蛙养在水缸里。
麦子黄了,父亲天天都会去地头瞧瞧,顺手揪下来几根麦穗,在手里一撮,看一看,再放进嘴里嚼一嚼,看麦粒是不是饱满,水分多不多。水分太多,收下来还要晾晒好久,也是不行的。
待收割那天,父亲会把家里的镰刀都找出来,在磨刀石上好好磨一下。那镰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样割麦子才利落。
那时候割麦子,大都是每人把着一垄麦,割好,也要放整齐,这样才好装车拉出去。父亲割麦子的速度是我的好几倍,常常是他很快就割了一半,我还没出地头,于是就会拿起水杯送给父亲,让他喝口水歇一会儿。然后和他商量:“爸,咱俩换换吧,你去割我割的那一垄,你割得快。”
每当这时,母亲都会数落我一阵,不让我耽误父亲割麦子。
那几年家里没有四轮车,也没有拖斗,父亲常常要从村头走到村尾,看谁家拖斗有空,能让我家用一下。于是,我家的麦子总是早早割了,拉出来却很晚。
那时候,我内心里憋了一口气,心里想着长大后一定不让父亲再作难,别人家有的,我家也要有。也为此,现在母亲常常笑我:“你小时候的志气都跑哪去了?还不如不长大,起码那时候还有点儿念想,现在可好了!”
麦子拉到场面上,就是打场、扬场、晒麦子……那时候,扬场是最不好玩儿的,因为风向会变化,常常把麦糠刮得满场都是,麦灰黏在身上是很痒的,非常难受。但父亲,每年都要这样重复着,虽有帽子、墨镜遮挡,但还是不行。扬场结束,一盆清水,父亲洗把脸就成了黑水。
近几年,大姐出嫁、我和妹妹在外工作,虽离家不远,但在农活上,连像儿时帮父亲母亲一把都没多少机会了。
现在有了大型收割机,不用割麦子、不用扬场,但家里那10亩地,几十袋子粮食,大多时候还是父亲搬上车,又卸下来的。如果再晒几次粮食,父亲又要多费几次力气。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粮食收了直接卖不行吗?何必这么麻烦!
是啊,我也这样问过,父亲母亲无非就是想等个好节点,让1斤小麦能多卖1毛多钱,10亩地能多卖千把块钱。
1斤1毛多钱,10亩地千把块钱,又有多少人会放在眼里呢?
父亲母亲会,而且这60多年来看得一样重。在他们眼里,这是一笔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