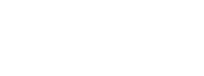在乡下,席是床的标配。轻轻薄薄的一领席,是乡下人居家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根据材质,席分蒲、苇、竹。在中原,最常见的是用高粱秸编成的席,普遍叫秫秆席。秫秆大多挺直修长,均匀顺滑,红绿白紫,饱满流畅。只需剔除弯曲矮断的,笼笼统统一大堆,先风干,后水泡,半干半湿的时候,铺上麦场,用石磙碾。这是硬功夫,也是成席的重要节骨点。套牲口拉,大材小用,打不开局面;人力推,脚下层层秫秆溜光圆滑,上肢难发力;一人推不动,人多站不下。最有效的办法是人站上石磙,双手撑棍拄地,缓缓启动,人用小碎步在石磙上跳着向前走,石磙稳稳往后转,先慢后快。在撑棍的“指点”下,沉重的石磙,来来回回,闪转腾挪,进退自如,功夫早已赶超了庙会上杂耍的水平。
编席是每家劳动力的基本功,如同犁耙耕种,收割拉打。碾就的秫秆,趁着润湿软和,先拿劈刀劈成批儿,再用篾刀抵紧压实,抽出一条条柔韧的席篾子。房前屋后,找块敞亮的地方,几捆篾子,一把编刀,三两天空闲时间,纵横交叉,切头收边,一领席,便端端正正编就了。
日常里,席是用来铺垫的,只求大小契合,里外耐用。放在床上,被褥有了保护,常年柔和;铺在地上,冬春阻寒,夏秋隔潮;睡在席上,四肢自如伸展,内心安稳妥帖。家里来了亲戚,生产队请了戏班,房不够住,床凑不齐,烟炕仓房,有的是地方,背几篓麦秸,丢上两捆席,来客便有了妥妥的安顿。若是逢着迎亲送喜,席便俨然成了家具嫁妆。选图案,定颜色,聘席匠,自然有了许多讲究。嫁女的,要踏席上轿,再不舍,离了席,与娘家自此有了交待;娶亲入户,先席后地,入了席,大姑娘嬗变成新媳妇。进了洞房,更是掉进了席的世界。床上铺的,顶上棚的,床围子,脚垫子,红席子,花席子,满屋的喜气,如和煦的春风,迎面扑来。
乡下人的一生都与席关联。因为,在他们生长的时候,大人们的主要精力都在庄稼上,哪顾得上一嘟噜的孩子。就在地头找块平坦的地方,不挨沟接水,铺领席,把他们按上去,任由坐爬翻滚;累了,不分席位领地,东倒西歪,随便俯仰卧趴。蚂蚱、蛐蛐、青虫子、白虫子、花大姐,把他们当成了温暖柔软的席,或闲庭信步,或激情与速度。有人睡梦中被弄痒了,小手胡乱抹两把,一翻身,又睡去了。臂上、腿上、背上,脸颊上、屁蛋上,一遍遍印满了席印子。顺嘴角涌出的涎水,拉出了明亮的长丝,正好是虫们的美食。他们的父母,没有谁会把这些当回事,喝水喘气的当儿,顺手把昆虫队伍清理了,像是摘掉了草籽泥巴。这样的日子年复一年,日不错影。无处躲避,也无须躲避。因为,风与尘土裹挟,席与大地研磨,早已把他们通身上下,里里外外,打磨出了黑黢黢油汪汪的包浆——也练就了他们席地而卧的童子功。
街头巷尾,宅门荒院;坑沿河边,埂上树下;打麦场,牲口屋,炕房里;泥地,草地,庄稼地;拉货赶脚,看瓜守秋。只要能放下领席,闲了席地而坐,累了倒头便睡。没有坐姿睡相,但求自在自处。年头久了,日虐风饕,如影随形的席印子成了他们的“金钟罩”“铁布衫”,即便寒暑错时,阴阳失位,也能从容应对。那领席,是身体的延展,如同他们的毛发皮肤、血肉骨骼,与生俱来,身去形消。命散归西,要先放在席上,把人世的最后时光,交于席,谓之“落薄席”,既生于斯,去也由斯。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生死大事,在他们眼里,如同草席一领。
一年之中,乡下人真正享受自然的时节,是在夏夜,在那张形影相随的秫秆席上。夏粮入仓,秋庄稼已抢茬种上。向晚落黑,溽暑消降,炊烟袅起;日沉月初,鸡鸭上宿,牛羊进圈。撂下碗筷,顺手打桶井拔凉水,把浑身的泥屑汗渍洗了。没有约定,男女老少各自从门口昏黄的灯影中晃了出来。拎席的,抱娃的,掂水壶的,挟铺盖的,一时间,大街小巷,影影绰绰,橐橐沓沓。最终,人脚旺至,汇到了村口的打麦场里。
这是席子的盛会期。长的,短的,净面的,花哨的,崭新的,破边的,连褥接席,骈肩抵足。孩童们翻人越铺,毫无顾忌。大人们或家长里短,或乡里流俗,话题似天上的云朵,浓淡远近,说来道去。昨夜,今夜,明晚;你家,他家,我家,总有说不完的流年碎影,道不尽的往事钩沉。即使是身下那领席,也往往引出无尽的念想,唏嘘的喟叹。
东邻那领席是他们成婚时的陪嫁,那可是请了方圆几十里最有名的席匠,花了十几天时间编就的,紫红紫红的“囍”字,十几年了,不变形,不掉色。对门家的那半领席,是他家头胎落地儿的产床。那一年,高粱大丰收,秫秸粗壮浑实,色醇皮厚,流光溢彩,仿佛上了一层釉,抽出的篾子像皮条一样。如今,孩子都快成家了,剩下的这片残席,依然像墙上的画一样,油光明亮。
夜色幽蓝,繁星晶亮。多少劳累烦忧,早随着渐次弱下的人声,化进清凉的夏夜,风流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