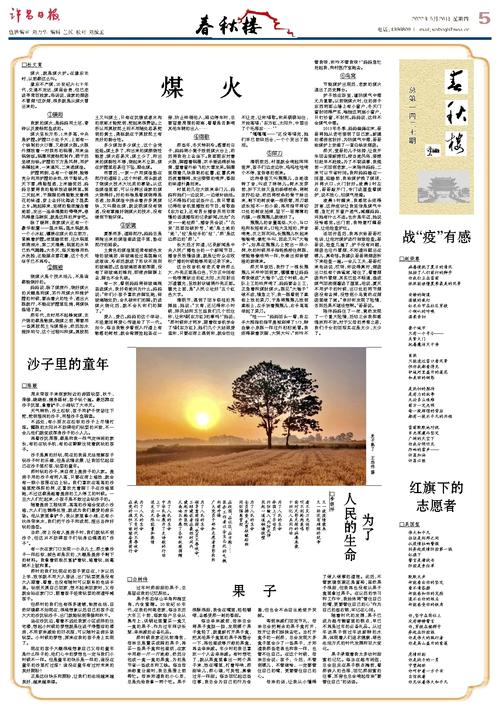煤火,就是煤火炉。在豫东农村,以前都这么叫。
豫东不产煤,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交通不发达,煤虽金贵,但已走进寻常百姓家。俗话说,谁家的烟囱不冒烟?这炊烟,很多就是从煤火冒出来的。
①暖洞
我家的煤火,是妈妈用土坯、青砖以及麦秸泥垒成的。
煤火呈长方形,1米多高,中央是炉膛。炉膛口小肚子大,上面有一个铁制的火口圈,又称煤火眼。火眼外摆放着一对弧形的锅圈,用来坐锅烧饭。锅圈用麦秸泥制作,晒干后坚硬如铁。炉膛的下方是风洞,用炉条隔起来,一来通风,二来透煤渣。
炉膛两侧,各有一个暖洞,能够充分利用炉膛的余热,烘干鞋袜。冬天下雪,棉鞋湿透,上床睡觉后,妈妈总要将我的鞋袜放进暖洞里。第二天起床,干蹦蹦的棉鞋散发着棉花的味道,穿上去好比踏进了温柔之乡。跑起路来,坚硬的鞋底撞击着地面,发出一连串清脆的嘚嘚声。春风得意马蹄疾,就是这样的声音吧。
除了暖洞,我家煤火还有一个豪华配置——温水锅。温水锅就是一个小水缸,镶嵌在煤火的左前方,紧挨着炉膛。夜里睡觉前,往水锅里添满凉水,第二天清晨,锅里的水早已热气腾腾。大冬天,每天能够用热水洗脸,还能搽点雪花膏,这个冬天似乎已不再冷。
②煤渣
烧煤火是个技术活儿,不是谁都能烧好的。
妈妈说,除了煤质外,烧好煤火的关键是和煤,另外用煤火杵捅炉膛的时候,要由着火的性子,透出火眼就行,不能在炉膛里乱捅,将煤块捣塌了架。
那年代,农村用不起蜂窝煤,农户烧的都是散煤。烧煤之前,需要用一些黑胶泥土与煤混合,然后加水搅拌均匀,这个过程叫和煤。黑胶泥土又叫煤土,只有在坑塘或者水沟的底部才能挖到,挖起来很费劲。之所以用黑胶泥土而不用随处容易挖到的黄土,奥秘就在于黑胶泥土有良好的黏合性。
多少煤加多少煤土,这个全凭经验。煤土多了,和出来的煤燃烧性能差,煤火容易灭;煤土少了,和出来的煤黏性不够,烧起来不立架,煤在炉膛里容易往下坠,屙生煤。
雨雪后,一家一户用煤渣垫在泥泞的道路上。这个时候,街头就成了烧煤火技术大比武的赛场。从这些煤渣里面,可以分辨出谁家的煤火烧得好。好的标准是看煤烧得是否透,如果煤渣中残余着许多黑煤块,又叫屙生煤,就说明煤没有烧透,没有掌握好烧煤火的技术,没有做到节能环保。
③玻璃
夏季雨多,道路泥泞。妈妈总是将掏出来的煤渣装进篮子里,垫在泥泞的路段。
土黄色的煤渣里经常有颜色发暗的玻璃团,碎玻璃经过高温融化成液体,冷却后就成了形状不规则的玻璃团。这些玻璃团表面浑圆,没有了碎玻璃的锋利,即便赤脚踩上去,脚也不会扎破。
有一次,看到妈妈将碎玻璃瓶丢进煤火,我好奇地问为什么。妈妈说:“你们小孩子喜欢赤脚乱跑,碎玻璃随处扔,会扎破你们的脚。扔进煤火烧化后,就不会扎你们的脚了。”
爱人,爱己。妈妈的这个举动,不经意间将爱心传递给了下一代。如今,每当我散步看到人行道上有散落的树枝,就会弯腰捡起丢在一旁,防止绊倒他人;路边停车时,总要留意周围的距离,看看是否影响其他车辆的出入……
④唱歌
那些年,冬天特别冷。落雪的日子,妈妈将小凳子放到煤火台上,然后将我抱上去坐下。我面朝东对着火眼,脚蹬着锅圈,双手插进棉袄袖筒,望着窗外纷飞的大雪发呆。锅圈里煨着几块蒸熟的红薯,红薯炙烤后流着糖稀,发出嘶嘶的响声,香甜的味道扑鼻而来。
村里的几位大娘来串门儿,妈妈和她们一边说笑,一边做针线活。记不得她们在说些什么,我只零星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节目,有歌曲《东方红》,还有男女播音员用非常慢的语速播报的记录新闻。比如“北京——地拉那”,播音员会说:“‘北京’后面加破折号,‘地’是土地的‘地’,‘拉’是拉手的‘拉’,‘那’是这边那边的‘那’。”
长大后才知道,记录新闻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新闻节目,播音员放慢语速,就是让听众在收听广播的时候能够用笔记录下来。
这台收音机有老式青砖那么大,外壳正面是白色,下方正中间有一轮喷薄欲出的红太阳,太阳射出万道霞光,呈放射状铺满外壳正面。霞光上面,是“人民公社好”五个红色大字。
清明节,遇到了回乡祭祖的秀婵姐,她说:“文育,还记得你小时候,排凤姑和玉兰姐我们几个拦住你,让你唱《东方红》的事吗?”她说:“那时候你才两岁,跟着收音机学会了唱《东方红》,她们几个大姑娘爱逗你,只要在街上遇到你,就会拦住不让走,让你唱歌。你呆萌萌站住,开始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嘎嘎嘎——”还没等唱完,她们早已前仰后合,一个个笑出了眼泪。
⑤菜刀
清明前后,村里就会响起阵阵笛声,孩子们边走边吹,呜呜哇哇响个不停,宣告春的到来。
这种春笛又叫篾篾儿,当地读转了音,叫成了咪咪儿。树木发芽前,折下又细又直的杨柳枝条,将树皮拧松动,然后将枝条的骨干抽出来,剩下的树皮像一根吸管,用刀裁成长短不一的小段,再用指甲将切口处的树皮掐掉,留下一层薄薄的内膜,一根篾篾儿就做好了。
篾篾儿的音量高低、大小,与口径和长短有关。口径大且短的,声音响亮,反之则沉闷。长篾篾儿吹起来嗡嗡响,像牤牛叫,因此又叫“大嗡子”。如果在篾篾儿上挖出一排小洞,吹的时候用手指轮换按住洞眼,便能够像唢呐一样,吹奏出抑扬顿挫的旋律来。
那天早饭后,我拧了一根长篾篾儿兴冲冲回到家,嚷嚷着让妈妈帮我做成“大嗡子”。这个时候,生产队上工的铃声响了,妈妈要去上工,正急着和煤封煤火。眼见“大嗡子”做不成,情急之下,我一眼看到了案板上放的菜刀,于是将篾篾儿放到案板上,左手扶着篾篾儿,右手高高举起了菜刀。
“哇—— ”妈妈回头一看,我左手大拇指的指甲盖被剁掉了1/3,鲜血像小泉眼一样往外汩汩地冒。我疼得跺着双脚,大哭大叫:“你咋不管我呀,你咋不管我呀?”妈妈急忙抱起我,向村医疗室跑去。
⑥鸟窝
节能煤炉出现后,老家的煤火退出了历史舞台。
炉子放在卧室,谨防煤气中毒尤为重要。以前烧煤火时,住的房子东西两面山墙上有小窗户,冬天门窗封闭得严实,唯独这两扇小窗户,只钉纱窗,不封死。妈妈说,这样不会煤气中毒。
2013年冬季,妈妈偏瘫在床,哥哥将她从老宅接到了自己家。新建的楼房密封好,为防煤气中毒,哥哥给煤炉上安装了一套白铁皮烟囱。
那天,堂哥的儿子结婚,让我开车回去接新媳妇。按当地风俗,接媳妇赶早不赶晚。为了不耽误事,我提前一天回到老家,一来陪伴妈妈,二来可以节省时间。我和妈妈睡在一间屋,临睡前,我给煤炉换了煤球,并将火口、火门封好。凌晨2时左右,哥哥敲开门,专门进屋查看煤炉,说不放心,怕煤气泄漏。
凌晨5时醒来,我感觉头疼得厉害,这种症状让我坚信是煤气中毒,急忙打开窗户透气。喊醒妈妈,问她有什么不适。也许是年迈,她说没啥感觉。出门前,我特意叮嘱哥哥,让他检查炉灶。
返回许昌后,我再次给哥哥打电话,让他对煤炉进行细致检查。哥哥说,检查几遍了,炉子没有问题,烟囱也往外冒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真奇怪。我建议哥哥将烟囱拆下来检查一遍。一会儿工夫,哥哥打来电话说,哎呀,你说得真对,烟囱出口处有个麻雀窝,堵住了,看着烟囱向外冒烟,其实已经不畅通,造成煤气回流倒灌进了屋里。他说,夏天不用炉子的时候,出口处的两节烟囱没有去掉,没想到小鸟竟然在烟囱里做了窝。“幸好你发现了险情,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哥哥说。
陪伴妈妈住了一夜,竟然发现了一个重大险情,后怕之余我深感愧疚和不安。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们子女的回报实在是太少,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