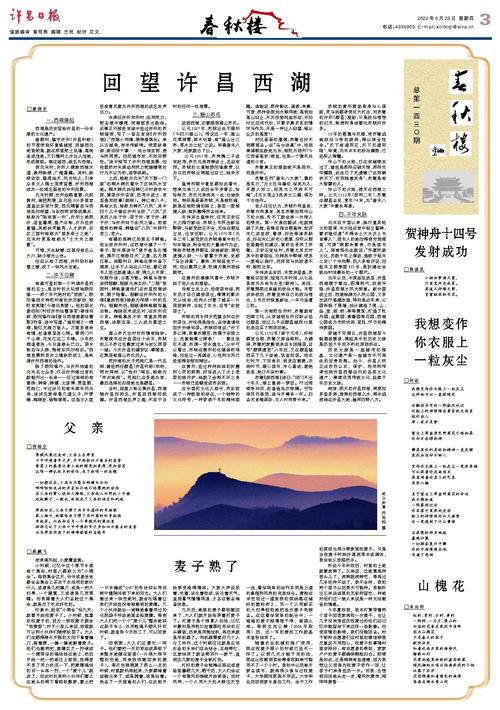一、西湖缘起
西湖是历史留给许昌的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
唐朝时,镇守许州(许昌时称)的节度使曲环重修城垣,因城西北地势较高,就在那里挖土筑墙,高岗遂成洼地;又引潩河之水注入洼地,形成湖面。湖在城西,故名为西湖。
到北宋时,许州人疏浚西湖水道,栽种杨柳,广植莲藕。其时,杨柳依依,碧荷连天,风光怡人,引来众多文人雅士观赏留墨,许州西湖成为一处闻名遐迩的中州胜景。
北宋时期,许州战略重要:北扼黄河,南控荆楚,东北经200多里官道直达东京汴梁,西北隔嵩岳与西京洛阳相望,与东西两京势成鼎足,被称为“陪京第一州”;许州土地肥沃,适宜灌溉,盛产谷物,亦为经济重镇;其地钟灵毓秀,人才济济,东汉三国时被称为“固多奇士之地”,北宋时更是被称为“士大夫之渊薮”。
可惜,天生缺憾,这里没有名山大川,缺少湖光山色。
但自从有了西湖,许州弥补缺璧之憾,成了一块风水宝地。
二、许下公卿
有案可查的第一个吟诵许昌西湖的名士,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那个年代绝对的“顶流”。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被贬官夷陵(今湖北夷陵)。他的朋友谢伯初(时任许州法曹参军)寄信问候,欧阳修作诗《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作答,诗中写道:“遥知湖上一樽酒,能忆天涯万里人。万里思春尚有情,忽逢春至客心惊。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春头已白。异乡物态与人殊,惟有东风旧相识。”西湖美景和思友之情跃然纸上,是咏诵许州西湖的佳作。
除了欧阳修外,与许州结缘的北宋名士众多,仅在许州做过官的就能列出一长串——任过宰相的有晏殊、韩绛、韩缜、文彦博、贾昌朝、范纯仁,中过状元的有宋庠宋祁兄弟,诗词名家有晏几道父子、叶梦德、梅晓臣、钱惟演等。这些文人宦臣有意无意为许州西湖的成名发声出力。
宋庠任许州知州时,征用民力,挖去湖中横堤,使湖面多出数倍。此事正巧被赴京途中经过许州的苏轼碰到,写了一首五言诗《许州西湖》:“西湖小雨晴,滟滟春渠长。来从古城角,夜半传新响。使君欲春游,浚沼役千掌……池台信宏丽,贵与民同赏。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诗中描写了许州西湖美景,但他显然对宋庠动用民力挖掘横堤的行为不以为然,语带讽刺。
之后,被称为北宋“天下第一门族”的桐木韩氏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桐木韩氏始祖韩亿少时游学中原,寓居许州苦读,后考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副相)。韩亿有八子,具有文名,被称为韩氏“八凤”,其中四个儿子曾在许州主政,“八凤”及其后人生于许、居于许、官于许、葬于许,与许州结下生死之缘。前面提到的韩绛、韩镇在“八凤”中排行老三、老六。
有趣的是韩亿的第五子韩维。他主政许州时,在西湖中建了一个亭子,取宋庠诗句“凿开鱼鸟忘情地,展尽江湖极目天”之意,名为展江亭。闲暇时日,韩维在亭中备下酒席,让手下人站在入口处,看见读书人经过就邀请入席,满九人开席,饮酒作诗,日落方散。韩维与理学宗师程颢、程颐兄弟交好,“二程”贫困时,韩维邀请他们在许昌西湖讲学,朝夕陪餐。程颢在许州作的七律《重游西湖》被称为传颂一时的名作。程颢死后,程颐请韩维题写墓志铭。梅晓臣未成名时,在许州任小吏。韩维慕其才学,常邀其同游西湖,诗歌互答,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眉山苏氏也对许州情有独钟。苏辙晚年在许昌居住十余年,苏轼的儿子苏过也搬家过来与叔父同居一城。今天许昌的建安区、鄢陵县,还聚居有眉山苏氏后人。
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是一代名相,曾经两任颍昌(许昌时称)知府,两次拜相,以“俭朴”闻名,被称为“布衣宰相”。范纯仁在多地为官,最后选择的归宿地也是颍昌。
当时,冠盖人物云集许昌,西湖随许昌而知名,许昌因西湖而妩媚。许昌西湖名声之盛,不亚于当时的任何一处湖景。
三、眉山苏氏
说到西湖,还要提到眉山苏氏。
公元1037年,苏轼出生于眉州(今四川眉山)。传说这一年,眉山花草凋零,树木枯萎,有“眉山出三苏,草木为之枯”之说。毕竟唐宋八大家,他家就占了仨。
公元1057年,苏洵携二子进京赶考,苏氏兄弟同榜进士,名动京师。苏轼的文章被欧阳修激赏,认为日后苏轼必将超过自己,独步天下。
皇帝和朝中重臣都如此看中,想来兄弟二人此后会平步青云;恰恰相反,苏氏兄弟终其一生,仕途坎坷。特别是哥哥苏轼,不是被贬谪,就是在被贬谪的路上,甚至一度被捕入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宋神宗当皇帝时,任用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法,苏轼上书抨击新法弊病,与新党政见不合,无法在朝廷立足,出京任职。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新党抓住苏轼奏章中的几句牢骚话,附会他的大量诗作为证,弹劾苏轼愚弄朝廷,诽谤新政,将他逮捕入狱,一心要置于死地,史称“乌台诗案”。最终,苏轼虽免于一死,但以戴罪之身,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
在黄州的凄凄风雪中,苏轼开始了他人生的渡劫。
没有立足之力,他借居寺庙,两年后才自己建房居住;微薄的薪水无以活命,他向人讨要了城东一片荒坡耕种,当起了农夫,自号“东坡居士”。
苏轼的同乡师友范镇当时在许州居住,对他很是挂念,去信邀请他回许州做邻居。苏轼回信说,“许下多公卿,我蓑衣箬笠,放荡于东坡之上,岂复能事公卿哉?……要且坚忍不退,所谓一劳永逸也。”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在黄州的处境虽然艰难,但经过一再调适,心性和文风已经变得坚韧而阔达。
在黄州,经过种种肉体的折磨和心灵的煎熬,好似进入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苏轼已经蝶变成苏东坡。
在中国的文化人格中,苏东坡成了一种极致的存在,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一种穿透千年的精神图腾。谁能说,那种豁达、通透、率真、可爱,那种低到如水银泻地,高到如高山仰止,不为权势利益所动,不怕付出任何代价,只要求真求实的情怀与作为,不是一种让人仰望、难以企及的高度?!
对比哥哥的遭遇,苏辙也好不到哪里去。在“乌台诗案”中,他因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被贬为筠州(今江西省高安)酒监,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
苏辙真正的渡劫地不是筠州,而是许州。
苏辙名列“唐宋八大家”,靠的是实力,“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古文观止》选其文三篇,俱为千古佳作。
世人往往认为,苏轼外向直言,苏辙内向寡言,其实苏辙如同冰山下的火焰,冷不丁就会来一次惊人的喷发。第一次参加殿试,他就捅破了天庭,笔锋自指当朝皇帝,批评宋仁宗怠政、奢侈、好色等诸多缺点,好在宋仁宗宅心宽厚,没听从朝臣罢黜他的建议,竟然也录用了苏辙。王安石变法时,苏辙尤其反对其中的青苗法,论辩其中弊端,使其一度难以施行;后终因与执政者不和,被贬出京。
宋神宗去世后,宋哲宗登基,苏辙被召回京,短短几年时间,从七品县官升为尚书右丞(副相)。其间,苏辙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宋哲宗亲政后,苏辙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上书反对恢复新法,一年内连遭三贬。
第一次被贬汝州时,苏辙就有后顾之忧,从京城到汝州任职必经过颍昌,他让儿子在颍昌城西30里的泉店买了两顷田地。
公元1102年(崇宁元年),奸相蔡京当朝,苏辙又接连被贬。为避祸,苏辙把家搬到泉店乡间隐居,自号“颍滨遗老”;5年后,又在颍昌城西买了几十亩地,筑室而居。他农忙时节,下田务农,到泉店割麦;农闲时节,潜心读书,专心著述,谢绝宾客,绝口不谈时事。
苏辙《游西湖》诗曰:“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行过闾阎争问讯,忽逢鱼鸟亦惊猜。可怜举目非吾党,谁与开尊共一杯。归去无言掩屏卧,古人时向梦中来。”
苏轼的黄州渡劫是身与心俱疲,灵与肉都承受巨大打击,而苏辙的许州(颍昌)渡劫,只是政治理想的幻灭,物质和身体要比苏轼好许多。
10年的落寞与沉潜,使苏辙远离政治斗争的旋涡,得以保全性命。“天下有道则见,天下无道则隐”,毕竟,北宋末年的政治腐败,已经深入骨髓。
冰山下的火焰,已在京城喷发过了,曾经是那样石破天惊,那样光华耀眼,此生已了无遗憾!“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辙是有大智慧的人。
冰山下的火焰,熄灭在西湖之畔。公元1112年(政和二年),苏辙在颍昌去世,享年74岁,为“唐宋八大家”中最长寿者。
四、千年文脉
北宋自开国以来,施行重武轻文的国策,宋太祖在宫中秘立誓碑,要求继任者“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读书人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可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陈寅恪先生就说:“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个中利弊,后人多有评说,但赵宋王朝享国319年,是封建社会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
北宋以后,中原战乱迭至,许昌西湖疏于管治;明清两代,政局平稳,许昌西湖才风光渐复。新中国成立后,西湖被辟为人民公园,又多次进行修建改造,特别是近年来,公园拆除了围墙,设计建造了堤、山、岛、堂、阁、桥、亭等景观,打造了牡丹园、盆景园、紫薇园等花园,西湖公园成为市民休闲、览胜、怀古的精神家园。
穿越千年烟云,许昌西湖至今能碧波荡漾,绵延其中的历史文脉是历经千年而不朽的原因所在。
历史文脉是一座城市的根基,文化遗产是一座城市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如今,许昌人民正在孜孜以求,保护、利用和传承包括许昌西湖在内的各类文化遗产,赓续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千年历史文脉。
相信,明天的许昌西湖,将更加多姿多彩;潋滟的西湖之水,将永远流淌在许昌大地,遍布四野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