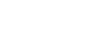□ 张云
红花草,不仅能佐餐,饥荒年代,还充当过食物。老辈人讲,一年水灾,住在低地的何家,杂物漂了一院。何家老太太拄着拐杖,立在齐腰深的水里号啕大哭。青壮年用菱桶将老太太接到高处,安顿下来。幸亏那不怕水的红花草,在青黄不接的冬春时节,拌着不多的米粒,帮他们熬过了那场饥馑。
红花草对土壤的要求不高,江南的一场秋雨就催发了它。星星点点的绿,稀稀落落地撒满田畦。一下雨,土路和了泥,泥浆没过脚面,一脚下去,四溅开来,裤腿、褂襟上的泥点有铜钱那么大,摔一跤,便成了泥猴子。怕妈妈骂,孩子们就朝红花田里蹚,洗净了裤脚,外带着一股草的好闻的气味儿。被踩得东倒西歪的红花草,蹭满细腻的泥,在大片的墨绿中,横开几道任性的褐黄。天晴,阳光一晒,褐色随着水汽蒸腾。下一场雨,倒伏的草梗慢悠悠地挺直了身子,泥顺着叶面往地下滴,湿漉漉的。被踩撞出的小径和缓平顺,隐没在红花草里。
春来,红花草渴急了似的拼命吮吸雨水,蓬勃地铺展开来。层层叠叠的叶片上,银色的水珠从这片滑到那片,珠子被传递好几次——他们玩倒手的游戏,把一个珠子玩腻了,任由其往地上滴,洇入泥中。天水满荒满野地落着,没人阻拦,总玩总有。
雨停,脱掉笨重冬装的孩子们,试探着将白脚丫往冰凉的红花田里插,一下,两下,三下,踩了进去。藏草吧!有人建议。有孩子背过身去,另一群用镰刀在红花田里挖坑,填一把莎草、麻子草,盖上泥土,踩平。再挖一处,弄得松松垮垮,伪装一下,喊一声“好嘞”。找者便开始寻,到处挖。红花田千疮百孔。
孩子总是爱贪玩儿,那么多没完没了的游戏等着,到太阳偏西,才想起还没割猪草,匆忙捡起镰刀,直奔邻村红花田,东张西望地割,心里怦怦直跳。“谁家的孩子,又来偷草?”孩子似受惊野兔,跳上泊在岸边的小船,镰刀柄向岸上一杵,船破一河春水,嬉戏着回家。
江南的春天,空气都湿漉漉的。雨停下的时候,田头的红花草已经没过孩子的脚踝开了花。一丁一点儿的粉紫,稀稀落落地开着,微小平摊的火把一般招惹蜜蜂。某一天,绿毯似的田野里,如颜料桶,一大片一大片,浓密的地方酡紫,稀疏的地方粉紫,清新鲜亮,不扎眼。有村子,便有采花的女孩儿,一根线摊在桌上,将花儿挨个儿排上去,两头连起来一扎,做成花球。随便往哪儿一挂,看着闻着,心里头欢喜。
雨季一过,房檐上的青苔干了。葡萄架上,垂下一串串青葡萄。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间漏进来,在井台留下斑驳的影子。玩累了的花猫躲进葡萄架的阴影里,伸展四肢,打个哈欠,蜷在一根朽桩边睡了。屋门前,刷衣用的水泥板滚烫。狗卧在客堂的青砖地上,伸长舌头闭眼喘着。弄堂口,老太太靠在竹椅上,摇蒲扇,摇着摇着不动了,嘴大张着。男孩儿见了,作势要将手中的泥蛋投进去,笑出声来。老太太醒了,骂了句什么。男孩儿们呼啦跑散,狗抬了抬眼皮。
这时,红花草鲜嫩娇俏的花,捧出豌豆模样的细荚,几天就被阳光照老了。鬼剃头一般的田垄间,没被割收的红花草,落寞地站着,等着太阳将绿色一点儿一点儿收回去。垄沟水,咕噜咕噜流进田沟,淹没了收割后松软的大地。
天,一日比一日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