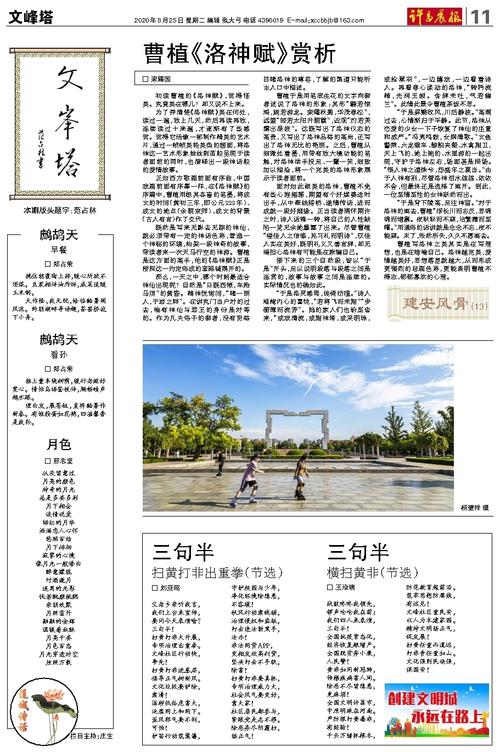□ 梁耀国
初读曹植的《洛神赋》,觉得怪美。究竟美在哪儿?却又说不上来。
为了弄清楚《洛神赋》美在何处,读过一遍,放上几天,然后再读再放,连续读过十来遍,才逐渐有了些感觉。觉得它活像一部制作精美的艺术片,通过一帧帧美轮美奂的画面,将洛神这一艺术形象抽丝剥茧般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同时,也演绎出一段神话般的爱情故事。
正如西方歌剧前面有序曲,中国戏剧前面有序幕一样,在《洛神赋》的序篇中,曹植用极其吝啬的笔墨,将成文的时间(黄初三年,即公元222年)、成文的地点(余朝京师)、成文的背景(古人有言)作了交代。
既然是写来无影去无踪的神仙,就必须带有一定的神话色彩,营造一个神秘的环境,构架一段神奇的故事,带读者来一次天马行空的神游。曹植是这方面的高手,他的《洛神赋》正是按照这一约定俗成的套路铺展开的。
那么,一天之中,哪个时刻最适合神仙出现呢?自然是“日既西倾,车殆马烦”的黄昏。精神恍惚间,“睹一丽人,于岩之畔”。在讲究门当户对的过去,唯有神仙与君王的身份是对等的。作为凡夫俗子的御者,没有资格目睹洛神的尊容,了解的渠道只能听主人口中描述。
曹植于是用笔底生花的文字向御者述说了洛神的形象:其形“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远望“皎若太阳升朝霞”,近观“灼若芙蕖出渌波”。这既写出了洛神仪态的高贵,又写出了洛神品格的高尚,还写出了洛神无比的艳丽。之后,曹植从细微处着墨,用带有放大镜功能的笔触,对洛神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细致加以描绘,将一个完美的洛神形象展示于读者面前。
面对如此淑美的洛神,曹植不免有些心旌摇荡,期望有个好媒婆适时出手,从中牵线搭桥、递情传话,进而成就一段好姻缘。正当读者满怀期许之时,诗人话锋一转,将自己的人性缺陷一览无余地暴露了出来。尽管曹植“嗟佳人之信修,羌习礼而明诗”,叹佳人实在美好,既明礼义又善言辞,却无端担心洛神有可能是在欺骗自己。
接下来的三个自然段,皆以“于是”开头,足以说明段落与段落之间是连贯的,故事与故事之间是连续的。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
“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诗人难掩内心的喜悦,“若将飞而未翔”“步蘅薄而流芳”。她的家人们也纷至沓来,“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一边嬉戏,一边看着诗人。再看春心漾动的洛神,“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此情此景令曹植茶饭不思。
“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高潮过去,心情渐归于平静。此节,洛神从恋爱的少女一下子恢复了神仙的庄重和威严。“冯夷鸣鼓,女娲清歌。”文鱼警乘、六龙载车、鲸鲵夹毂、水禽翔卫,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一起出现,守护于洛神左右,场面甚是排场。“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由于人神有别,尽管洛神泪水涟涟、依依不舍,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到此,一位至情至性的女神跃然而出。
“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对于洛神的离去,曹植“浮长川而忘反,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念念不忘、夜不能寐。末了,怅然所失,久久不愿离去。
曹植写洛神之美其实是在写理想,也是在暗喻自己。洛神越完美,爱情越美好,思想落差就越大,从而形成更强烈的悲剧色彩,更能表明曹植不得志、郁郁寡欢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