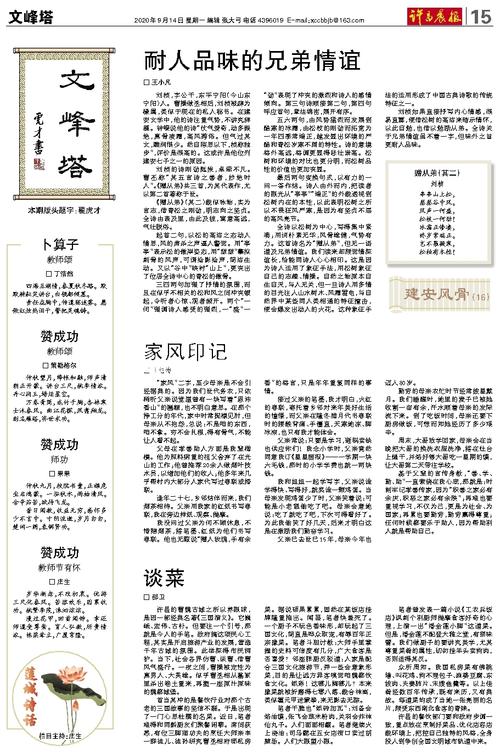□ 王胜涛
“家风”二字,至少母亲是不会引经据典的。因为我们世代务农,只依稀听父亲说堂屋曾有一块写着“恩沛香山”的匾额,也不明白意思。在那个挣工分的年代,家中时常捉襟见肘,但母亲从不抱怨,总说:不是咱的东西,咱不拿。穷不会扎根,得有骨气,不能让人看不起。
父母在孝善助人方面是我辈楷模。他为照料病重的祖父舍弃了在光山的工作;他曾推荐20余人做烟叶技术员,以增加他们的收入;他多年来几乎帮村内大部分人家代写过春联或婚联。
逢年二十七,乡邻结伴而来,我们烟茶相待。父亲用我家的红纸书写春联,我在旁边抻纸、观察、揣摩。
我没问过父亲为何不顾休息,不惜赔烟茶,搭笔墨、红纸为他们书写春联。他也无暇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格言,只是年年重复同样的事情。
接过父亲的笔墨,我才明白,火红的春联,寄托着乡邻对来年美好生活的憧憬,而父亲在隆冬腊月代书春联时的腰酸背痛、手僵直,天寒地冻、脚冰凉,也只有我才能体会。
父亲常说:只要是学习,砸锅卖铁也供应你们!我念小学时,父亲竟然同意我订《星星画报》——一学期一块六毛钱,那时的小学学费也就一两块钱。
我和姐姐一起学写字,父亲说谁学得快、写得好,就奖谁一颗鸡蛋。当母亲发现鸡蛋少了时,父亲笑着说:可能是小老鼠偷吃了吧。母亲会意地说:吃了就吃了吧,下次可得看好了。为此我偷笑了好几天,后来才明白这是在激励我们勤奋学习。
父亲已去世已15年,母亲今年也迈入80岁。
勤劳的母亲农忙时节经常披星戴月。我们睡醒时,地里的麦子已被她收割一亩有余,汗水顺着母亲的发际流下来。到了吃饭时间,母亲还要下厨房做饭,可想而知她经历了多少艰辛。
周末,大哥放学回家,母亲会在当晚把大哥的换洗衣服洗净,搭在灶台上熥干,并烙好够大哥吃一星期的馍,让大哥第二天带往学校。
基于父辈的言传身教,“善、学、勤、助”一直萦绕在我心底,那就是:时刻牢记孝善传家,因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再难也要重视学习,不仅为己,更是为社会、为国家;再累也要勤劳,勤劳赢得尊重;任何时候都要乐于助人,因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