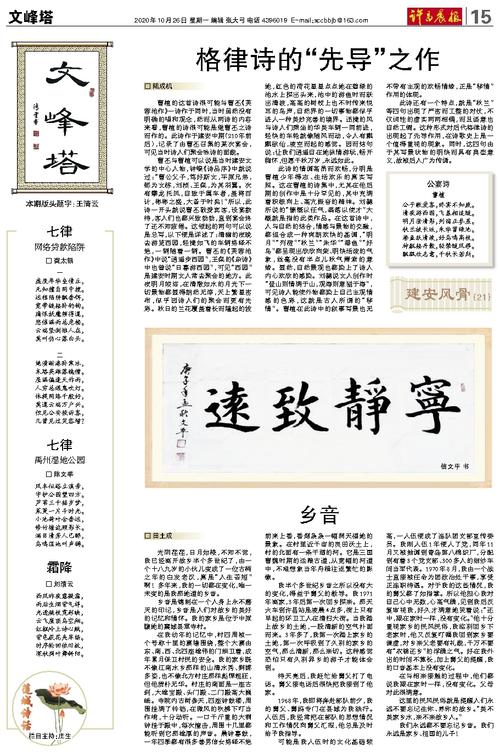□ 田土成
光阴荏荏,日月如梭,不知不觉,我已经离开故乡半个多世纪了,由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儿变成了一位古稀之年的白发老汉,真是“人生苦短”啊!多年来,我的一切都在变化,唯一未变的是我那地道的乡音。
乡音是镌刻在一个人身上永不磨灭的印记,乡音是人们对故乡的美好的记忆和情怀。我的家乡是位于中原腹地的襄城县草寺村。
在我幼年的记忆中,村四周被一个号称十里的寨墙围绕,整个大寨由东、南、西、北四座雄伟的门拱卫着,成年累月保卫村民的安全。我的家乡既不像江南水乡那样的山清水秀、婀娜多姿,也不像北方村庄那样彪悍粗狂,但他质朴无华。村庄的南面是一座古刹,大雄宝殿、头门殿、二门殿高大巍峨。寺院内古树参天,四座钟鼓楼,周围挂满了铃铛,在微风的吹拂下叮当作响,十分动听。一口千斤重的大铜钟挂于殿中,每次撞击,周围十几里都能听到它那雄厚的声音。晨钟暮鼓,一年四季都有很多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前来上香,香烟袅袅一幅洞天福地的景象。在村里近千亩的良田沃土上,村的北面有一条干涸的河。它是三国曹魏时期的运粮古道,从宽幅的河道中,不难想象当年舟楫往返繁忙的影像。
我半个多世纪乡音之所以没有大的变化,得益于舅父的教导。我1971年离家,3年后第一次回乡探亲。那天火车到许昌站是凌晨4点多,街上只有早起的环卫工人在清扫大街。当我踏上故乡的土地,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3年多了,我第一次踏上家乡的土地,第一次呼吸到了久别的家乡的空气,那么清新,那么亲切。这种感觉恐怕只有久别异乡的游子才能体会到。
待天亮后,我赶忙给舅父打了电话。舅父接电话后很快把我接到了他家。
1968年,我即将奔赴部队前夕,我的舅父、舅妈专门在县城为我践行。入伍后,我经常把在部队的思想情况和工作情况向舅父汇报,他总是及时给予我指导。
可能是我入伍时的文化基础较高,一入伍便成了连队团支部宣传委员。我刚入伍1年便入了党,同年11月又被抽调到青岛第八棉织厂,分配到有着3个党支部、300多人的细纱车间当军代表。1970年8月,我由一个战士直接被任命为团政治处干事,享受正连职待遇。对于我的这些情况,我的舅父都了如指掌。所以他担心我对自己心中无数,心高气躁,见到我后反复审视我,好久才满意地笑着说:“还中,跟在家时一样,没有变化。”他十分重视家乡的民风民俗,我临别回乡下老家时,他又反复叮嘱我回到家乡要谦虚,对乡亲父老要有礼貌,千万不要有“衣锦还乡”的浮躁之气。好在我外出的时间不算长,加上舅父的提醒,我的口音基本上没有变化。
在与相亲接触的过程中,他们都说我跟在家时一样,没有变化。父母对此很满意。
这里的民风民俗就是提醒人们永远不要忘记生你、养你的故乡。“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
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乡音。我们永远是家乡、祖国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