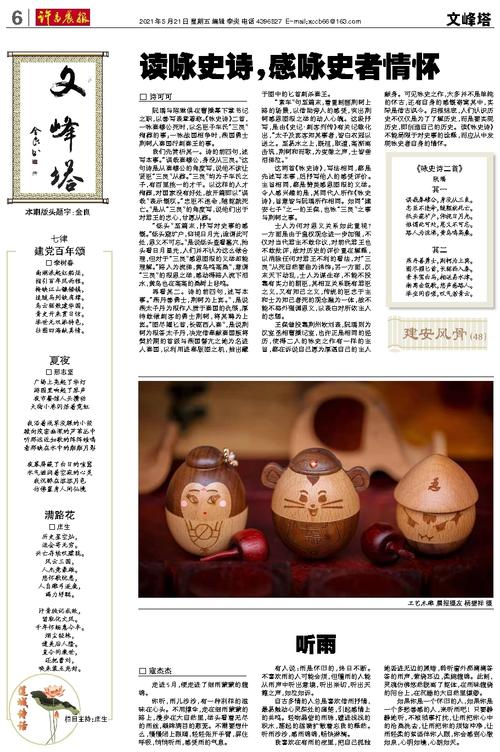阮瑀与陈琳俱在曹操幕下掌书记之职,以善写表章著称。《咏史诗》二首,一咏秦穆公死时,以名臣子车氏“三良”殉葬的事;一咏战国相争时,燕国勇士荆轲入秦国行刺秦王的事。
我们先赏析其一。诗的前四句,述写本事。“误哉秦穆公,身没从三良。”这句诗是从秦穆公的角度写,说他不该让贤臣“三良”从葬。“三良”均为子车氏之子,有百里挑一的才干。以这样的人才殉葬,对国家没有好处,故开篇即以“误哉”表示慨叹。“忠臣不违命,随躯就死亡。”是从“三良”的角度写,说他们出于对君王的忠心,甘愿从葬。
“低头”至篇末,抒写对史事的感慨。“低头窥圹户,仰视日月光;谁谓此可处,恩义不可忘。”是说低头查看墓穴,抬头看日月星光,人们并不认为这么做合理,但对于“三良”感恩图报的义举却能理解。“路人为流涕,黄鸟鸣高桑”,意谓“三良”的报恩之举,感动得路人流下泪水,黄鸟也在高高的桑树上悲鸣。
再看其二。诗的前四句,述写本事。“燕丹善勇士,荆轲为上宾。”,是说燕太子丹为报作人质于秦国的仇恨,厚待敢做刺客的勇士荆轲,将其聘为上宾。“图尽擢匕首,长驱西入秦”,是说荆轲为报答太子丹,决定借奉献秦国叛将樊於期的首级与燕国督亢之地为名进入秦国,以利用进奉版图之机,抽出藏于图中的匕首刺杀秦王。
“素车”句至篇末,着重刻画荆轲上路的场景,以借助旁人的感受,突出荆轲感恩图报之举的动人心魄。这段抒写,是由《史记·刺客列传》有关记载化出,“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
这两首《咏史诗》,写法相同,都是先述写本事,后抒写他人的感受评价。主旨相同,都是赞美感恩图报的义举。令人感兴趣的是,其同代人所作《咏史诗》,旨意皆与阮瑀所作相同。如同“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也咏“三良”之事与荆轲之事。
士人为何对恩义关系如此重视?一方面是由于皇权观念进一步加强,不仅对当代君主不敢非议,对前代君王也不敢批评,故对历史的评价重在解释,以消除任何对君王不利的看法,对“三良”从死自然要曲为讳饰;另一方面,汉末天下动乱,士人为谋生存,不能不投靠有实力的朝臣,其相互关系既有君臣之义,又有知己之义,传统的臣忠于主和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融为一体,故不能不格外强调恩义,以表白对所依主人的忠悃。
王粲曾投靠荆州牧刘表,阮瑀则为汉室丞相曹操记室,也许正是相同的经历,使得二人的咏史之作有一样的主旨,都在诉说自己愿为厚遇自己的主人献身。可见咏史之作,大多并不是单纯的怀古,还有自身的感慨寄寓其中,实际是借古讽今。归根结底,人们认识历史不仅仅是为了了解历史,而是要实现历史,即创造自己的历史。读《咏史诗》不能局限于对史事的诠释,而应从中发现咏史者自身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