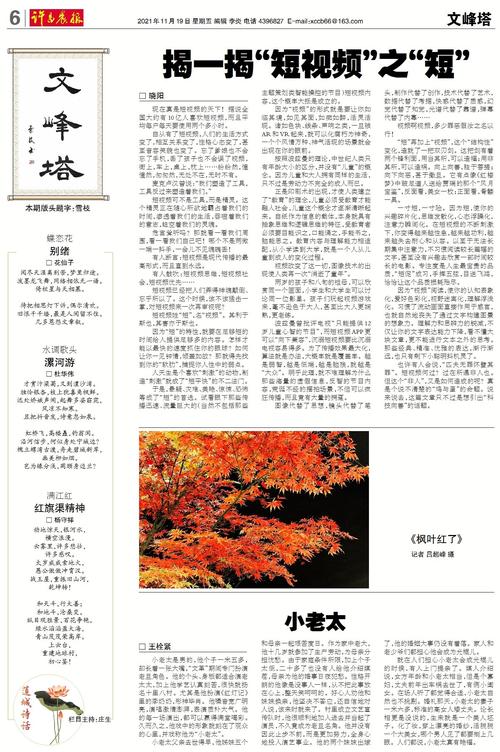现在真是短视频的天下!据说全国大约有10亿人喜欢短视频,而且平均每户每天要使用两个多小时。
自从有了短视频,人们的生活方式变了,相互关系变了,性格心态变了,甚至音容笑貌也变了。忘了爹娘也不会忘了手机,丢了孩子也不会误了视频,街上,车上,桌上,枕上……纷纷然,惶惶然,匆匆然,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麦克卢汉曾说:“我们塑造了工具,工具反过来塑造着我们。”
短视频可不是工具,而是精灵。这个精灵正在随心所欲地霸占着我们的时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吞噬着我们的意志,蛀空着我们的灵魂。
危言耸听吗?那就看一看我们周围,看一看我们自己吧!哪个不是两微一端一抖手,一会儿不见魂魄丢!
有人断言:短视频是现代传播的最高形式,而且直到永远。
有人鼓吹:短视频思维,短视频社会,短视频优先……
短视频已经把人们弄得神魂颠倒、忘乎所以了。这个时候,该不该猛击一掌,对短视频来一次再审视呢?
短视频姓“短”,名“视频”。其利于斯也,其害亦于斯也。
因为“短”的特性,就要在足够短的时间给人提供足够多的内容。怎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抓住你的眼球?如何让你一见钟情,倾盖如故?那就得先找到你的“软肋”,捕捉你人性中的弱点。
人天生是个喜欢“刺激”的动物,制造“刺激”就成了“短平快”的不二法门。
于是,悬疑、灾难、美艳、惊悚、恐怖等成了“短”的首选。试看眼下那些传播迅速、流量巨大的(当然不包括那些主题策划类智能操控的节目)短视频内容,这个概率大抵是成立的。
因为“视频”的形式就是要让你如临其境,如见其面,如痴如醉,活灵活现。诸如色块、线条、声响之类,一旦被AR和VR起来,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一个个风情万种、神气活现的场景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
按照波兹曼的理论,中世纪人类只有年龄大小的区分,并没有“儿童”的概念。因为儿童和大人拥有同样的生活,只不过是劳动力不完全的成人而已。
正是印刷术的出现,才使人类建立了“教育”的理念,儿童必须受教育才能融入社会,儿童这个概念才逐渐清晰起来。自纸作为信息的载体,本身就具有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特征,受教育者必须要目能识之,口能诵之,手能书之,脑能思之。教育内容与理解能力相适配,从小学读到大学,就是一个人从儿童到成人的变化过程。
视频改变了这一切,图像技术的出现使人类再一次“消逝了童年”。
两岁的孩子和八旬的祖母,可以欣赏同一个画面,小学生和大学生可以讨论同一位影星。孩子们玩起视频游戏来,毫不逊色于大人,甚至比大人更娴熟,更老练。
波兹曼曾批评电视“只能提供12岁儿童心智的节目”,而短视频APP更可以“向下兼容”,沉溺短视频要比沉溺电视容易得多。为了传播效果最大化,算法就是办法,大概率就是覆盖率。越是弱智,越是低端,越是脑残,就越是“大众”。明乎此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海量的虚假信息,反智的节目内容,荒诞不经的摆拍场景,不但可以疯狂传播,而且竟有大量的拥趸。
图像代替了思想,镜头代替了笔头,制作代替了创作,技术代替了艺术,数据代替了考据,快感代替了质感,幻觉代替了知觉,光谱代替了靠谱,弹幕代替了内幕……
视频啊视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短”再加上“视频”,这个“结构性”变化,造就了一把双刃剑。这把剑有着两个锋利面,用当其所,可以造福;用非其所,可以造祸。向上向善,胜于菩提;向下向恶,甚于撒旦。它有点像《红楼梦》中跛足道人送给贾瑞的那个“风月宝鉴”,反面看,美女一枚;正面看,骨髅一具。
一寸短,一寸险。因为短,使你的兴趣碎片化,思维发散化,心态浮躁化,注意力瞬间化。在短视频的不断刺激下,你变得越来越性急,越来越功利,越来越失去耐心和从容。以至于无法长期集中注意力,不习惯阅读较长篇幅的文字,甚至没有兴趣去欣赏一部时间较长的电影。专注度是人生最宝贵的品质,“短促”成习,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恰恰让这个品质损耗殆尽。
因为“视频”阅读,使你的认知表象化,爱好色彩化,视野迷离化,理解浮浅化。习惯了流动画面直接作用于感官,也就自然地丧失了通过文字构建图景的想象力。理解力和思辨力的锐减,不仅让你的文字表达能力下降,看不懂大块文章,更不能进行文本之外的思考。那些经典、精准、优雅的表达,渐行渐远,也只有剩下小聪明抖机灵了。
也许有人会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短视频何过?过在所遇非人也。但这个“非人”,又是如何造成的呢?真是个说不清楚的“鸡与蛋”的命题。说来说去,这篇文章只不过是想引出“科技向善”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