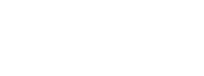□一和
繁城是一座古镇,镇上有一条五里长街,有东街、西街、南街、献街、清街5个村,是一处回汉杂居的地方。外婆家在繁城镇南街,三间秦砖汉瓦的正屋,东西两侧各有两间厢房,是土坯砌墙、麦秸搭顶的草房。
外公姓牛,是近六尺高的壮汉。据母亲讲,外公的祖上是繁城镇首屈一指的富贵人家,无奈外公年轻时嗜赌如命,输得只剩下几亩赖以活命的薄地和几间房子,侥幸被划成了贫下中农。数年以后,赢了外公钱财、酒楼、土地、粮行、房屋的大地主孔寨首被一粒子弹送上西天,临刑前呼天抢地地喊:“是你害了我呀,牛保寨!”那便是声讨他的对家、我外公呢。因此,外公常常在外婆面前沾沾自喜地说:“若不是我好赌,若不是我每赌必输,你能过今天的安稳日子吗?这叫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也。”
的确,外公是一个很有学问、很有先见之明的人,这从他一个女儿、四个儿子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来。外公又是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男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愣是坐在家里活活饿死了。那时候,母亲已出嫁,父亲是许昌农场管喂猪的工人,我大舅、三舅的性命正是因为一次次跑到农场偷吃猪食才得以保住。但是,我外公不愿意在他的女儿、女婿面前偷偷摸摸地吃猪食。其实,这又算什么呢?在那个非常年代,为了活命,别说是偷吃猪食了,即使偷吃别人家的菜团儿,抢别人手中的窝头,也没人讥笑你的。但是,外公不愿意,宁愿饿死也不干。我外婆说:“知道吗?好外孙,这叫气节!人可以没有饭吃,可以没有衣裳穿,却不可以没有气节。”
在繁城,外婆不叫外婆,叫姥娘;外公也不叫外公,叫姥爷。
因为有了妹妹,我从三岁起便被寄养在外婆家。在外婆家,我属于重点看护对象,除了在隔壁牲口屋和一个同龄的矮个儿男孩儿玩,几乎很少独自到别的地方去。舅舅们不让我出去,外婆也对我紧张兮兮的,说是外面乱,怕丢了我这个好外孙。外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家闺秀,出嫁时嫁妆摆了足足有二里路,两只笋一样白净的小脚,比三寸金莲还精致。每当我撒开脚丫子朝五里长街飞跑的时候,外婆便迈着小脚一点一点地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轻轻地喊:“小祖宗,你给我回来,看我不打烂你的屁股。”也许是家教的缘故吧,外婆从不骂人,也不像别的女人一样扯破了嗓门大声喊。即使这样,我一次也没得逞过,总是有人在靠近五里长街的牛家祠堂附近把我截获,交到外婆手中。外婆呢,一只手抓着我的小胳膊,另一只手便在我的屁股上不疼不痒地打一下,然后拽着我回家。这天,我休想再踏出院门半步。
有一天上午,吃过饭,舅舅们上工去了,外婆还在灶火里忙碌。我说:“姥娘,你忙吧,我去牲口屋找顶棒玩去!”外婆说:“去吧!别乱跑,别和顶棒打架。”我答应着就出门了。到了牲口屋,我才发现顶棒不在,只有一个远房舅舅正在给牲口续草。我问:“舅舅,顶棒呢?”这个远房舅舅看我一本正经的小大人模样非常搞笑,哄我说:“顶棒啊,周公领着去北京看热闹了。”那一年,我四五岁,不知道这个远房舅舅是逗我玩呢,更不知道北京在哪儿,可我想,既然名字叫北京,既然周公能够领着顶棒去北京,那北京一定离这儿不远,一定在牲口屋的北面。于是,我从牲口屋出来,向北,顺着巷道,一路慢慢悠悠地朝北京去了。
繁城只是一座古老的小镇,可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是天底下最大的一座城。我从牲口屋出来,顺着巷道一直往北走。走啊,走啊,我走到一处坐落在高台上的大院跟前,看见好多人在那儿聚集,一群穿绿军装、戴绿军帽、套红袖箍的大哥哥、大姐姐正在搭建一座很高很高的戏台。我以为这里就是北京了,且真的有好戏,于是就在戏台前停了下来。
“戏”是吃过午饭开演的。开演时,我饿着肚子坐在一棵弯腰柳树的枝杈间。本来我想留在戏台上,可那个管台子的大哥哥不让,说:“小屁孩儿,凑啥热闹,滚蛋!”没办法,我只能爬到戏台前的柳树上。柳树下聚了好多看热闹的人,大喇叭嗡嗡作响,我正犹豫着要不要下去撒泡尿再上来,突然听到扩音器里爆出一声大喊:“把某某某押上来!”紧接着又喊:“把高帽子给他戡上去!”我一惊,感觉裆里一紧,尿不由自主地就蹿了出去,洒到下面一个陌生男子头上。那男子板着脸,咬牙切齿地说:“小兔崽子,你下来!看我不捶死你。”我吓坏了,紧紧抱着树干盯着他,想哭又不敢哭,生怕他一怒之下爬上来,或者用砖头砸我。这样僵持了好大一会儿,他看我不下去,终于失去了耐心,转过脸,跟着人群呼喊起来。
我俯视着他,希望他把我忘掉,或者换一个地方去喊叫,这样我就有机会逃跑了。那一刻,我甚至想,那些穿绿军装、戴绿军帽、套红袖箍的大哥哥若是能过来,把他绑到台上去,该有多好!可是他不动,也没有一丁点要走开的意思,我只能老老实实地蹲在柳树的枝杈间,非常沮丧又满怀希望地等待他离开。头上戴高帽、胸前挂着大牌子的是几个面黄肌瘦、战战兢兢的男人,有戴眼镜的,有不戴眼镜的,都和外婆年纪差不多。夕阳西下时,戴高帽、挂大牌子的几个男人被押下戏台,押进高台上的大院。树下长相凶狠的男子仰脸瞪我一眼,说:“小心我揍你!”然后就跟着人群到院子里看热闹去了。我看着他走远,从树上滑下来,顺着来路一溜烟地往回跑。
外婆吓坏了。我跑回外婆家时,看到她正坐在院子里握着脚脖子号啕大哭呢,两位本家的妗妗在一边劝慰着她。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外婆跟前,说:“姥娘,你哭什么呢?”外婆闭着眼睛呜呜咽咽地说:“我的好外孙儿丢了,我怎么不哭呢?”两位妗妗看见我,吃了一惊,异口同声说:“回来了,这不回来了?”外婆抹一把泪,把我揽进怀里,说:“小祖宗,你跑哪儿去了?”我说:“我去北京看戏去了。”
被外婆派出去找我的舅舅们是喝罢汤后陆陆续续回到家中的。大舅最后一个回来,说:“今天戴高帽的杨校长回到家就上吊自杀了。”我不知道上吊自杀是怎么一回事,追问大舅,他不耐烦地说:“就是弄根绳把自己吊死了。”我不认识字,不知道戏台上哪一个是杨校长,可我想,杨校长和我外公一样,是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男人吧。
外婆病逝于1995年,享年86岁。现在,年轻人很少有人知道高帽子这回事了,但是,它像外婆给我的爱一样,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怎么挥也挥不去。偶尔,上了年纪的人会说,别给我戴高帽子了,那意思是别夸我、别抬举我了,很有一点儿黑色幽默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