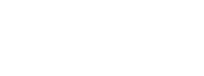驻村第一天,单位领导把我送到村里,与村里交接完就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了距许昌180里的这个山村。我在村部的住室里发了一会儿愣,突然感觉自己像只身远嫁的小媳妇,孤单的涟漪在心里一圈圈荡漾开来。
下午,村支书老赵领着我在村里转,一边走一边给我介绍村里的情况。这是个省定贫困村,初次见面,老赵就把村里想干的事说了一大堆,听得我头皮发麻。修路、打井、河坝清淤、建文化广场……这些事我都听说过,却没干过。山村的确与平原村庄不一样,没个正街,盖房子随着山势,哪个朝向都有。我转晕了,迷失了东南西北,忘了来时的路。老赵呵呵笑着说:“咱村的房子盖得有点儿歪七八扭。”我强挤出一丝笑容回应他:“我觉得是错落有致。”
天色将暮时,我们回到了村部。我准备做饭了。“娘家人”是铁了心让我在这儿过下去了,液化气灶、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大米挂面、榨菜老干妈准备得整整齐齐。我一边归置一边想:娶妻生子二十年,一朝变成单身汉。老赵进来对我说:“别忙活了,俺跟你嫂子说过了,走,去俺家喝玉米糁去,就着酸红薯叶,你不知道多美!”我心里一惊:这是真穷啊!这年代了连白面还保证不了,还要吃红薯叶。我推辞,老赵说:“别呀!做的有你的饭,你不去就剩下了,家里又没喂猪,倒了可惜。”我只能去了,老赵家里没喂猪,我不能头一天就糟蹋群众的粮食。
天上没有月亮,挂着几颗时隐时现的星星。前一天刚下过雨,路上有泥也有水。老赵教我夜里走泥路的技巧——黑泥白水紫花路,黑色的是稀泥,明晃晃的是水,不黑不白的地方才能下脚。我一边睁大双眼寻找脚下的紫花路,一边想着即将喝进嘴里的玉米糁。虽然没有经历过“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饥饿年代,可我对杂粮也不感兴趣。我在家里喝过玉米糁,淡而无味还拉嗓子。路上经过老赵说的要清淤的河坝,残存的水面上倒映着几点星光,我心里突然有点儿潮湿,阿炳的二胡曲《二泉映月》幽咽着弥漫开来。
老赵把《二泉映月》强行切换了。他紫花路倒是走得很熟,一边走一边从兜里掏出了一台唱戏机,选了一首歌循环播放起来:香茶一盏迎君到,星儿摇摇,云儿飘飘,何必西天万里遥。欢乐就在今朝,欢乐就在今宵……这是电视剧《西游记》里树精、花精捉住唐僧时唱的欢歌,我摸了摸自己的光头,唉,宝宝心里苦呀!
深一脚浅一脚,上坡下坡,拐弯抹角终于到了老赵家。一进院子,嫂子就从厨房迎了出来:“赶紧上屋吧!玉米糁一会儿就熬好了。”年近六旬的老赵不修边幅,脸上沟壑纵横,嫂子却是干净利索,头发烫得曲曲弯弯,比老赵贵气多了。
老赵家面朝北三间平房,阳台下摆着三个铁丝网编的大圆笼子,里面装满了金黄色的玉米棒子。老赵指着玉米笼子跟我说:“这样放着不生虫,吃一点儿,磨一点儿。”还真是长年吃呀!进到堂屋刚坐下,嫂子就在厨房里喊:“老赵,你去洞垴上拿几骨朵蒜。”老赵出去了,沿着厨房边上的楼梯噌噌上了房顶,过了一会儿又回到了堂屋。我没话找话:“你这房子盖得不错。”老赵说:“这三条洞箍10多年了。”“你刚才去哪儿了?”我问他。他手指向上指了指说:“洞垴上。”“洞垴是哪儿呀?”我又问。老赵一脸费解:“洞垴就是洞垴呀!”片刻后恍然大悟,说:“哦哦哦,洞垴就是房顶。”我苦涩地笑了,问:“明明是三间房,为什么叫三条洞?明明是房顶,为什么叫洞垴?”老赵哈哈一笑,说:“祖祖辈辈住窑洞说习惯了,改不过来了。”
嫂子端着一盘像梅菜一样的黑色菜叶进来了,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酸红薯叶了。老赵一边起身一边说:“你别动,我去端汤,你不知道多美!”看这架势,我一会儿不美出鼻涕泡儿,老赵满意不了。玉米糁汤端上来了,一股鲜玉米棒子的香气扑面而来。汤呈金黄色,不太像我之前在家里喝的那种玉米糁,倒像是南瓜汤。我让嫂子坐,嫂子不坐,老赵说山里的女人来客不上桌。嫂子不坐也不走,站在旁边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说:“你尝尝。”
四目睽睽之下,我端起了碗。汤上面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油皮,吹开油皮,汤里面如同勾了芡,微小的玉米糁悬浮其中,乡间称这种状态为乱糊。喝进嘴里,谷物特有的醇香立刻在唇齿间打了个回旋,口腔里如沐春风。那些微小的玉米糁非常糯,像是果粒橙里的果冻,可以直接咽下去,也可以扁扁嘴把它们化开,化开后瞬间满口生津。汤刚进嘴时是香的,待滑过喉头时有了一丝微甜。酸红薯叶是鲜红薯叶自然发酵而成的,经此转化叶子变得劲道,叶梗变得脆嫩,用线椒、小葱、香油一拌,鲜得不可方物。玉米糁醇厚,酸红薯叶凛烈,二者的确是绝配,如同辽阔的海面上数只水鸟在追随着一头时浮时潜的鲸鱼,又如一支乐曲先以舒缓柔和的管风琴开场,接着小提琴华丽嘹亮的声音破空而来,瞬间变得激越。这么说吧!我一口气喝了两碗玉米糁,也没注意老赵什么时候放的筷子,自己把那盘酸红薯叶快吃完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更准确地说是一方水土出产的食物养一方人。山地灌溉不便,耐旱的玉米就以更醇香的味道养育着山里的人。我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弱点,只要饭吃好了,心情就会变得愉悦。老赵和嫂子满面笑容地看着我,看我放下了碗,老赵说:“再盛一碗吧!吃吧,吃饱了不想家!”这个老赵,话不能说得含蓄点儿吗!
驻村是一场奇遇,遥远的山野、陌生的人突然闯入我的生活,和我的生命有了紧密的联系。我驻村两年半,老赵最初设想的那些事我们一起都做了。如今村里装上了路灯,夜里再不用走紫花路了。我又回到了从前的生活之中,其实是回不去了。我的胃隔一段时间就会提示我它想吃某种东西。我搜索脑海里关于食物的所有记忆,寻找它到底想吃什么,就像是在通信录里找一个一下子想不起名字的熟人。我总会在一瞬间醍醐灌顶,想到我是想吃两口酸红薯叶、喝一碗鸠山玉米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