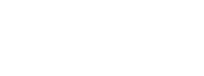我的干娘去世了,享年99岁。这个比我大一甲子还多的老人,在历经一个世纪变迁、遍尝人世间各种滋味后,最终撒手人寰,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没有人能说清干娘是哪里人,就连她自己也记不住了。八岁时,她遇上打仗,跟着大人逃难,一路逃到我们这里,饿晕在干爷爷家门口,管她口饭吃,便成了干爹的童养媳。长大后,她回去找过娘家,又遇上花园口决堤,极目之内皆是黄水,娘家已不复存在,自此便没了根。
干娘姓柳,没有大名,在娘家小名叫絮儿。干爹姓杨,二人成婚后,她便有了自己的官称——杨柳氏。如果把小名续上,就是杨柳絮,很诗意的一个名字。可惜她不识字,一辈子答应着,却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怎么写,直到立碑时才能把名字郑重地刻下来,这也是她应该得到的认可。
我儿时体弱多病,奶奶反复托人央求干娘,恳请她认我当干儿子,希望我能够养得活、留得住。干娘让人把我抱过去,看了看长相,摸了摸后脑勺,说:“我娃儿脑袋后面长着大把子,将来肯定有大出息!”于是,我就成了她最小的儿子。时年,她66岁,我一岁。她的亲儿子们管她叫妈,我管她叫娘。
小时候,逢年过节我常去干娘家串门,特别是我生日和祭灶那两日是必去的。通常,干娘会早早地坐在门口的大柳树下等我,一手拖着根拐棍儿,一手摩挲着怀里的老猫。看到我来了,她便会放下猫,撇开拐杖,迈着小脚三步并作两步地迎上来,紧紧地攥住我的手,也不言语,只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生日那天,她会早早地煮上红皮鸡蛋,待我到了用笊篱捞出来,在我头顶绕着圈滚动,一边滚一边碎碎念,祈求神灵保佑我健康成长。祭灶那天,她会把灶神请出来,备上些祭品,上香焚纸放鞭炮,并让我跪下磕头,最后把酥糖拿给我吃,让我享受这难得的福缘。
长大后,老家回得越来越少,干娘的消息也越来越少,我只有在年底回去拜年的时候,到她家里坐一会儿,问问她的身体情况和年岁收成。而她,仍如我年少时一般,算着我要回去的日子,早早地拄着拐棍儿等在大门口,眼巴巴地盼着她的小儿子归来。当我来到她跟前时,她用苍老的双手摩挲我的脸颊,过上好一会儿才说:“我的娃儿好着嘞,越来越壮实了。”
我考上大学那年,只顾高兴着疯玩,忘记回老家告诉干娘了,直到过春节时才想起到她家里坐坐。她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我考上了大学,在我回去的前一天晚上,从箱底摸出一枚康熙大钱,就着灯光用红线编了一夜,编出一个佩饰来。我到干娘家时,她双眼通红,颤巍巍地将那佩饰系在我的腰上,嘴里念叨着:“我娃儿有出息,考上状元了呢,是天上的文曲星嘞!娘这八十多年活得值当了。”
干娘一辈子就进过一次城,就是我结婚那次。坐了几十公里的汽车,她也不嫌累,甚至顾不上坐电梯带给她的惊悸,连口水都不肯喝,念叨着要看她的儿媳妇。儿媳妇娶进门,她先掀开盖头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然后牵着儿媳妇的手说:“我娃儿有福嘞,娶了个好媳妇,我放得下心啰!两口子要好好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呢。”
最后一次见干娘,是在今年的清明节。我回去给奶奶添坟,干娘半倚在门口的藤椅上,因患了白内障,眼睛看不见了,耳朵也聋得厉害,跟她说话要很大声。我攥住她的手,还没来得及说话,她便激动起来,大声地喊着:“娃儿!娃儿!你回来看老娘了!老娘高兴着嘞!”过了片刻,她又严肃起来,说:“娃儿,在官府里干公差,要听毛主席的话,做个干净人,你干净了,老娘就是死了也能放心去了。”没想到,这段话成了干娘对我最后的叮咛。
老娘过世后,年过古稀的大哥打电话给我报丧,未曾言语,已泣不成声,我也久久说不出话。人的一生,被一位母亲抚养照顾已是幸福,我却有两位母亲,何其有幸!
唢呐声声,如泣如诉。回忆起干娘的碎碎念,我又难以自禁,潸然泪下。干娘,倘有来生,还盼在您膝下承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