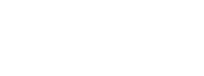李俊瑶
今年暮春,我随河南省杂文名家采风团到了禹州,感觉进入了古镇古村的窝儿。禹州我去过多次,可熟悉的都是“钧都”“药都”“夏都”这些符号性的东西。禹州市委书记王宏武在介绍时不无自豪地说:“禹州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这句话让人浮想联翩,故事都是过往,都与历史有关,除了躺在博物馆里、睡在地方志里的,应该还有藏在其他地方的,比如禹州的古村。
车从喧闹的市区进入西部山区,我们走过几个静谧的古村,如张家庄、李金寨、天垌村等。它们虽然位置不同,但都姓“古”,气质也相差不大。静,是它们的状态;慢,是它们的节奏。山外人到此,那颗躁动的心会渐趋平静,“古树高低屋,斜阳远近山”的诗情与遐思会悄然滋生。
遐思一:我租住在这里怎样
在鸠山镇西部的张家庄村,路边的一幢石头建筑吸引了我。进去一看,有正房、东西厢房,均为红石砌就,敦实而规整,只是空空荡荡,徒有四壁。当时一个念头冒出:我退休后租住在这里怎样?于是,开始各种脑补:大门建成什么样的?家具也入乡随俗吧?有互联网吗?带来的发烧音响适应这里的电压吗?附近得开个菜园吧?还得养几只鸡。对了,必须养条藏獒。
好好的房子怎么就空了呢?屋子的主人呢?哦,一定是去外面闯世界了。也难怪,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被大量吸往城市,有想法的青壮年不是随着家乡的小河漂泊向东,就是沿着绵延的山路一路向南。于是,空巢越来越多,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成为普遍现象。
有点特色的古村,正是在这种人去楼空的过程中渐渐衰败了。参观的过程中,我不时听到有人说“老刘家的大树都伐了”,“老张家的古门楼也拆了,要不还是有点看头儿的”,话中满是惋惜。是啊,古村里留存着许多历史积淀,如古建筑、千年习俗、农耕文明的记忆……有的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因为人口逐年外流,生机也渐渐流失,尤其是流传千年、曾经稳固城乡二元结构的乡绅阶层,早已断代,不复存在。
那么,假如我租住在这样的古村,只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环境吸引,却面临诸多不便,如交通不畅、水源不足、供电不正常、网络信号弱,时间长了,我会感到被现代文明越抛越远,不也会再次搬离吗?
著名作家冯骥才曾经痛惜地说:“中国每天都有近百个古村在消失。”怎么办?就这样听任古村淹没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就这样听任文化遗产湮灭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吗?
遐思二:古村如何延续根脉
如果农村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有方便的挣钱门路,有独特的文化基因、产业基因,我想很多人并不愿意背井离乡。那么,如何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如何留住乡愁呢?
古村保护,应该就是重拾乡愁的有效载体。但是,有学者感叹,保护古村比保护故宫还难!因为古村保护不仅涉及建筑、文化、观念等方方面面,还涉及智力投入、财力支撑。因为是“活态”保护,不能让“发展”与“保护”冲突,所以必须让古老景观与现代产业共生、民俗传承与时代精神共鸣。这样,新的发展才不会割断旧的根脉。
张家庄村就是重视古村保护的典型。石砌房、夯土墙、三进老宅,散发着古朴的味道。村口巨大的老槐树,诉说着这里的古老,也象征着不灭的生机。这里物产丰富、民风淳朴,红叶谷、白龙潭风光秀丽,可因交通闭塞,一度成为省定贫困村。近年来,通过扶贫攻坚,张家庄村靠山吃山,采取“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发展核桃、中药材种植和牛羊等特色饲养业。他们还修建了白龙潭水库,打深水井,建了提灌站,引水上山。水来了,灵气也来了。随着柏油路的通车,旅游业也火起来了。鲜槐花、山泉水,成了山外人抢购的商品,而红叶、老宅院更让这里游人如织。2018年,张家庄村入选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人涌来了,生机又回来了,古村的经济发展与根脉保护实现了微妙平衡。
遐思三: 整体搬迁的取与舍
为了修建三峡大坝,很多村庄整体搬迁。还种搬迁模式眼下正流行。比如山西省的一些老宅院、古建筑,正通过商家购买的方式,精细拆除,整体搬迁到外地,重获生机。这种搬迁模式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路:对于中西部的古村而言,如果自然环境已经恶化到不搬不行,如果古村已经失去产业依托和人气支撑,整体搬迁、精细搬迁、原物搬迁、原样重建,不失为古村“复活”的一种有效途径。
禹州市的李金寨村,就是整体搬迁的一个村庄。“树挪死,人挪活”,李金寨因搬得福。一排排别墅组成了一个新村,供水、供电、排污、绿化等,都达到了城镇化水平,这里还有简易的污水处理系统、垃圾分类系统。试想,农村也实施垃圾分类,在全国也为数不多吧?唯一不足的是,该村搬迁时没有进行原村复活,现代味儿较浓,乡情乡愁淡了些。
所以,我大胆设想,今后那些生机流失、不得不搬的古村古镇,若采取精细拆除、原样复原的整体搬迁模式,不但不会衰落,反而会因易地复活。那鸡鸣犬吠、青山绿水的乡景,那炊烟如岚、粉墙黛瓦的古村落画卷,一定不会在时代发展的光影中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