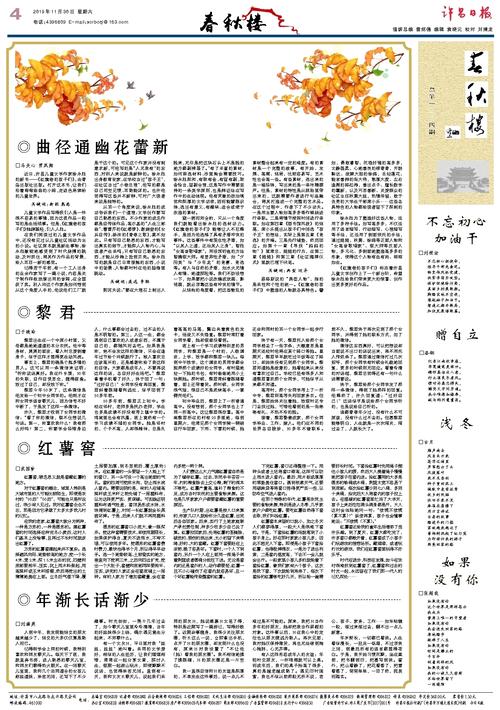□马炎心 贾凤翔
近日,许昌儿童文学作家徐永胜的新书——《红旗巷的孩子们》,由青岛出版社出版。打开这本书,让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走进色彩缤纷的儿童世界。 关键词:新颖 熟悉
儿童文学作品写得吸引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这类作品一般写的是生活琐事。但是,《红旗巷的孩子们》独辟蹊径,引人入胜。
在我们阅读过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还没有见过以儿童社区活动为主的小说。社区原本就是新生事物,徐永胜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脉搏的跳动,及时抓住,将其作为作品的背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记得若干年前,有一个工人出身的业余作家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是关于制作样板戏演出用的音箱,在全国获了奖。别人问这个作家是如何想到从这个角度入手的,他说他们工厂就是干这个的。可见这个作家并没有刻意求新,可他写的是“人无我有”的东西,对别人来说就是新鲜的。徐永胜出身教育世家,在学校当过“孩子王”,在社区当过“小巷总理”,他写的都是自己司空见惯、耳熟能详的。也许他觉得写这些并不新鲜,可对广大读者来说是独特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徐永胜的成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文学创作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不少作家的成名作都是自传体作品,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曹雪芹的《红楼梦》、谢婉莹的《女兵自传》、杨沫的《青春之歌》,莫不如此。只有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才能写出真实的细节,才能深入人物内心,与读者产生共鸣;只有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才能从沙滩上捡到贝壳。徐永胜写的就是自己日常接触的东西,小说中的场景、人物都时时在他的脑海里跳动。
关键词:遴选 串联
契诃夫说:“要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脸的地方都剔掉罢了。”有了丰富的素材,如何筛选材料、沙里淘金需要技巧。徐永胜深知,有取有舍,有留有剔,取舍恰当,留剔合理,这是写作中需要坚持的一条美学原则,也是辩证法在写作中的生动体现。他有灵敏的政治嗅觉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因而能慧眼识珠,选出有意义、有趣味、适合或便于改造的素材。
窥一斑而知全豹,只从一个角度我们就能看出徐永胜的选材功力。《红旗巷的孩子们》能够让人不忍释手,是因为他选择了具有矛盾冲突的事件。这些事件中有观念性矛盾,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智胜“女高音歌唱家”;用设饵钓鱼的方法智擒假大师。有差异性矛盾,如“夕阳美”与“少年龙”的竞赛、竞选等。有人与自然的矛盾,如水火无情人有情、地道探险等。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要把小说改编成戏剧、影视剧,就必须靠这些有冲突的情节。
从结构的角度看,把这些散乱的素材整合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有的素材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开始、发展、高潮、结局,比较容易写,艺术性也会高一些。有些素材,选出来的是一堆珍珠,写出来的是一串冰糖葫芦。但是,素材的特性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这就需要作者进行勾连融合,将其打造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下了不少功夫。一是用主要人物如高多多等作银线进行串联。二是将情节按照时间进行串联。如在第四章《图书馆风波》的结尾,席小乐提出从孩子们中间选“孩子王”的想法,实际上是第五章《竞选》的开端。三是先行铺垫,然后回应。如第十一章《寻找“妈妈的吻”》里常总、姥姥的行为,在第二章《姥姥》和第三章《社区揭牌仪式》里就已埋下伏笔。
关键词:典型 迥异
恩格斯说的“典型人物”,指的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红旗巷的孩子们》中塑造的人物就各具特色。譬如,勇敢睿智、沉稳好强的高多多,文静温柔、心地善良的柳青青,开朗豁达、泼辣大胆的徐鸽,舌灿莲花、能言善辩的张大伟,憨厚大度、左右逢源的路松涛,善出点子、擅长数学的霍新,以及巧思善断、关爱群众的社区主任秋菊大姐,热情洋溢、敢于负责的大学生干部席小乐……这些各具特色的人物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徐永胜为了塑造好这些人物,运用了多种手法。如写高多多,不仅运用了语言描写、行动描写、心理描写等手法,还运用了侧面烘托的手法,通过姥姥、秋菊、徐鸽等正面人物和“女高音歌唱家”、假大师等反面人物,多元化、多侧面地塑造高多多的形象,使得这个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红旗巷的孩子们》标志着许昌儿童文学创作上了一个新台阶,希望徐永胜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