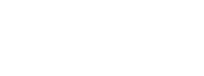□路来森
邻居家大门外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是柿树。
枣树上,结满了枣子;柿树上,结满了柿子。
枣树,果实是长圆形的,叫“长龄枣”。每年中秋节的前几天,邻居家就开始打枣了。年轻人爬上枣树,手持一根竹竿,朝四周密集的枣子扑打。于是,红艳艳的枣子散落一地。邻居家的人,在树下忙着捡枣。我们家的人,也帮着捡枣。枣捡完了,邻居就装上一大瓢,送给我们。
所以,那些年,每年中秋节晚上,我们家的饭桌上都有一碗蜂蜜蒸红枣。
打枣的时候,柿树上的柿子,还倔强地青涩着。
我们虽与邻居家比邻而居,可邻居家是农户,我们家不是。所以,邻居家有地种,我们家没有。
中秋节一过,就开始收秋了。
邻居家渐次把收割的高粱运回家,把掰下的玉米棒子拉回家。
高粱捆成捆儿,垛在墙边。玉米棒子剥去外皮,一根根系在一起,形成串,搭在大门外的歪脖子枣树上。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家一开大门,就能看到红彤彤的高粱穗儿和黄灿灿的玉米棒子。
这时节,也正是扁豆丰收的时候。一串串扁豆挂满墙头,邻居家的人几乎天天都会踩着凳子摘扁豆。人头高过墙头,一边摘一边与我们家的人闲聊。不少扁豆蔓越过墙头爬进我们家,邻居摘扁豆时就会说:“那边的,我们不摘了,你们摘吧。”很多时候,邻居家摘得多了,也会顺手把一些扁豆抛进我们家庭院中,说声:“接住了。”
时光,在色彩变换中流逝。邻居家开始摘棉花了。
在我的记忆中,摘棉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邻居家的主妇背一只布口袋,晴好的天气,每天都会下地,摘回来一口袋棉花。摘回来的棉花,要晾晒。在大门外摊开一大块塑料布,棉花就晒在上面。邻居家的老奶奶,负责看棉花。她手中拿一根竹竿,每隔一段时间,就用竹竿把棉花翻一遍,拍打几下。棉花越晒越白,棉花越拍越干净。
一些麻雀,飞到高粱捆儿上,飞到棉花上,老奶奶就挥动手中的竹竿,吆喝几声,麻雀顿时飞起,爪子上还粘着棉花丝,口中还衔着高粱籽儿。
有时候,我会站在自家庭院中看天。蓝色的天空中,有白云飘过,一朵朵、一团团。我觉得,那就是邻居家的棉花。
摘棉花的这段日子,邻居家的秋越来越深了。
墙头的扁豆,叶子渐渐枯萎下来,花不再开放。大门外,柿子树上的柿子,由青变黄,又由黄变红,颜色越来越诱人。
一场寒霜之后,墙头上的扁豆叶全蔫了。邻居家不管大小,将扁豆悉数摘下晒干,就叫作“霜扁豆”。霜扁豆,是冬日的美食,清炒之后嚼起来特别筋道,别有一种风味。
秋更深了,邻居家开始摘柿子了。柿子不能打,要一个一个地摘。用绳子系一个竹筐,将摘下来的柿子放进竹筐里,然后再把堆满柿子的竹筐缓缓地放下来。
摘柿子的时候,邻居家的老奶奶会站在树下,一边观看,一边吆喝:“不要全摘光,留下些柿子给鸟吃。”其实,不用吆喝,柿子也不会被摘干净。高高的树顶上的那些柿子,谁能够得着呢?也只好留着了。
留在树顶上的柿子,一直在秋风中摇曳,直到自然成熟,成为软软的烘柿。那是被秋阳“烘”熟的,越来越红,越来越艳,馋人得很。于是,那些年里,我常常做这样的梦:一个烘柿子恰好掉在我手中,我摘掉柿子蒂,用力一吸,甜甜的汁液流进口中……
邻居家的甜柿子,是秋天最后的味道,也是我记忆中最美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