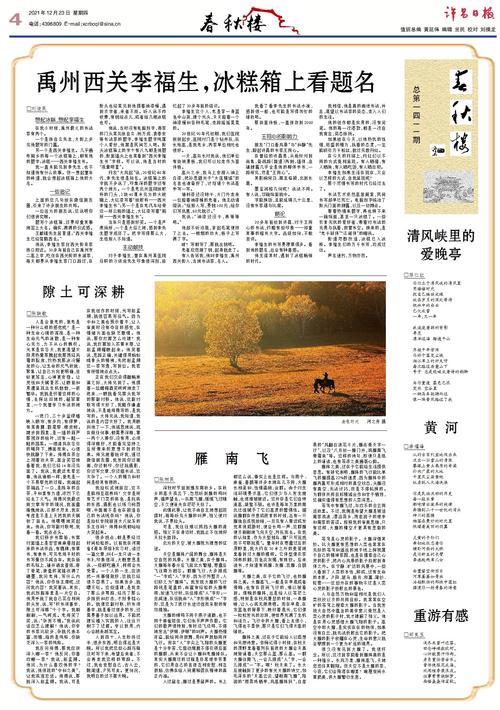想起冰糕,想起李福生
在我小时候,禹州最火的书法家有两个。
一个是张自立先生,大街上多见他题写的门匾。
另一个是西关李福生。几乎遍布城乡的每一个冰糕箱上,都有他的题字:冰糕——西关李福生书。
我一直未能见到李先生,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故事。但一想起童年的味道,就会想起冰糕箱上他的大名。
一些追记
上面的这几句放在微信朋友圈,引来了许多朋友的共鸣。
一位远方的朋友说:这说明你们很讲究啊。
题写个冰糕箱,还要郑重其事地签上大名。确实,满满的仪式感。
王献臻先生回复道:“西关李福生已经驾鹤西去。”
他说,李福生家住西关街田家拐口附近。30多年前自己在禹州市二高上学,吃住在西关街的亲戚家,每天都要从李福生家门口路过,在街头也经常见到他提着油漆桶,遇到求字者,来者不拒。听人说不咋收费,有钱给点儿,或者给几根冰糕也可。
他说,当时没有电脑刻字,商家的门头常见张自立、杨万成、袁泰安等书法家的题字,李福生题字纯属个人爱好,他算是民间艺人吧。街头冰糕箱上的字十有八九都是他题的,街面墙头上也常看到“西关李福生书”字样。可以说,他是当时的“流量明星”。
网友“大风起”说,20世纪80年代,李先生很是知名。冰糕箱上的字就不多说了,印象深的题字还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老北关医院放射科的门头,3块40厘米见方的大玻璃上,大红漆写着“放射科——西关李福生书”;另一个是在老汽车站旁边一所公厕的墙上,大红漆写着“厕所——西关李福生书”。
当年只是感到好笑。一个是严肃场所,一个是大俗之地,感到李先生题字成狂了。把字写得那么大,生怕别人不知道。
主动献技
对于李福生,曾在禹州某医院任职的刁训启先生印象很深刻,回忆起了30多年前的结识。
李福生这个人,老是穿一身蓝色中山装,理个光头,天天掂着一个油漆桶和各种毛笔,走路摇摇晃晃的。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医院刚刚起步,医院对门是个钻井队,队长姓高,是我老乡,两家单位相处也很好。
一天,高队长对我说,他们单位有块铁黑板,我们可以拉走作为宣传板。
高兴之余,我马上安排人油上白漆,把孙思邈关于“大医精诚”的名言也准备好了,计划请个书法高手写一写。
谁料漆还没晾干,大门外走来一位掂着油漆桶的老者。他主动请缨说:“给别人写,要钱100元,给你们写优惠,60元就行。”
我说:“油漆还没干,再等等吧。”
他却不听劝阻,拿起毛笔便抹了上去。一根烟的功夫,板子上写满了字。
唉!写都写了,那就出钱吧。
老者欣然接了钱,起身就走了。
有人告诉我,他叫李福生,禹州西关街人,当地书法家,名人。
我看了看李先生的书法水准,感到很一般,也可能是写得匆忙的缘故吧。
那块宣传板,一直保存到2000年。
王同心的影响力
朋友“门口看风景”与“和静”先生,聊起许昌的书家王同心。
在曾经的许昌县,从枪杆刘到尚集,备战路(国道)两侧,墙体、店铺牌匾几乎全是他的柳体手书,一路所见,尽是“王同心”。
其影响所及,南至临颍,北到长葛。
墨宝润格几何呢?说法不同。有人说,怼碗烩面就中。
字能换饭,且能延绵几十公里,没有书家堪与比肩。
略论
20多年前初到许昌,对于王同心的书法,约略有些印象——郑重其事的楷书大字。品级如何,不敢妄评。
李福生的书写要潦草得多。看到他的题名,总会有种喜感。
他生逢其时,遇到了冰糕畅销的时代。
我相信,他是真的痴迷书法,并且,渴望以书法家的姿态,走入人们的生活。
他的创作都是实用的,没有闲笔。他的每一次落款,都是一次自我肯定,姿态张扬。
如果放在今天,以他热忱的性情,旺盛的精力,执着的态度,一定能吸引万千粉丝,胜过无数网红。
在今天的网络上,网红们以不同的方式竞相呈现。有人晒猫,有人晒狗,有人晒吃饭,有人晒垃圾。
李福生如果生活在现在,又会以怎样的方式,自我呈现呢?
那个尽情书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书法艺术依然高居殿堂,民间书写却早已死亡。电脑刻字统治了街头门面的牌匾,以及一切摊点。
靠着热情来题字,再也换不来一碗烩面,甚至一只冰棍了。一些衣食无忧的爱好者,带着对书法的无畏与执着,寂寞书空。换来的,是“老干部体”“江湖体”的嘲讽。
街道尽数改造,冰糕已入冰柜。李福生们的万千书写,均成过往。
声名速朽,万物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