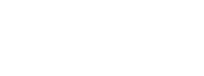智齿从春节前开始萌动,萌动的结果是给孕育他们的妈妈——也就是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都说“过年胖三斤”,这个年我瘦了十斤。最疼的时候,浆面条我都咬不动。
我虽然是个男的,但从孕育他们的角度讲,说我是他们的妈妈,我感觉更适合。作为一种物体,“他”字也许用指代动物的“它”更准确,但是我也不能生俩小动物呀,所以还是用指代人的“他”吧。
很长时间里,我都不知道“智齿”这个词。我长了一嘴好牙,白,颗颗均匀,圈形也好,笑起来特别阳光,牙齿是我颜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的牙齿结实而又健康,以前从来没有疼过,冷热酸甜吃多少,牙齿都平安无事,咬核桃、开啤酒瓶都不在话下。
智齿以疼痛的方式提醒了我他的存在。我对给他们命名的人很愤怒,这种坏蛋怎么能叫这么好听的名字呢,简直是向邪恶势力低头!还智齿,他们怎么就比其他牙聪明了?是说他们长期潜伏,然后突然窜出来破坏人类吃香喝辣的大好局面吗?我查了一下他们的命名原因,比较多的说法是说智齿位于口腔深处、牙床的末端,是人类最晚长出的牙齿。一个人长出智齿的时候,通常都心智成熟了,所以叫智齿。我想哭,我快50岁了,他们在这个时候长出来,不但伤害了我,而且羞辱了我。我要向以前所有被我伤害过的人道歉,对不起,请原谅一个心智不成熟的高龄儿童吧!
我还查到了一点“八卦”,说是智齿长出的年龄乘以4,就是一个人的寿命。年近半百的我是要往200岁上奔吗?要是这种说法属实,那说我现在还处于人生的少年时代,心智刚刚成熟倒也合适。再有10多年,我就要退休了,那会儿应该是刚进入青年。面对还有140年的人生,我干点儿啥呢?年复一年地领国家的退休金,真不好意思呀。也许过了110岁,我就可以卖票让全世界的人民来参观我,一方面实现我成为亿万富翁的梦想,另一方面或许会成为许昌的一个重要文旅资源,为许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智齿长出的疼痛时断时续。其实应该是一直疼的,不疼的时候,是他们吃了药。这些可恶的家伙是毫无廉耻的瘾君子,吃了药就安生,不吃药就闹腾。
这一周疼得整个上腭都肿了起来,之前吃的药量已经无法满足他们了。说话都疼,24小时疼,一天到晚就一个事——疼。也干不了别的事,干活的时候,一个人在一边不停地拧着你的脸,你说你能干成啥?实在是受不了了,我最讨厌受制于人或物,决定实施剖宫产,把他们拔下来。
约好了医生,到医院拍了口腔全片。片子中是我200年后的样子——一个长着森森巨齿的骷髅。
医生说智齿像阑尾一样,除了让你疼,对人根本没用,早该拔了。该拔了,我倒可怜起智齿来了。智齿命不好,生不逢时,早出来几年,位置往前排排,不也是口之栋梁,也能吃香喝辣吗?生得晚了,就成了多余,食物到他那儿都已经是渣;一出生就提心吊胆,刀斧之灾随时会加身。
医生说打麻药有点儿疼,拔牙不疼。
打麻药是真疼,一根小针在牙龈上下左右挑着扎。不一会儿,我的半边脸就木了,感觉嘴唇比非洲人的还厚。
拔牙开始了。我的嘴瞬间成了一个矿洞,叮当作响,各种轰鸣,医生像要把一块狗头金挖出来一样,在里面又是刨,又是钻,又是拔……那动静和钻头打磨牙时散发出的焦糊味儿,根本不像是在对待一张嘴。我的嘴里一定血污横流,一个医生拔牙,一个医生拿着一个“吸尘器”,在里面不停地打扫。最后上了钳子,医生按着我的头,钳子往下拽,仿佛我是一条眼镜蛇,死死咬住了他。
我的樱桃小嘴呀,你太可怜了。
历时半个小时,狗头金成功挖出。医生让我看那两颗牙。他们是冰山,露出水面的是一小部分,埋在肉里的部分无比硕大。要是等他们全长出来,我得疼死好几回。牙龈上缝了几针,刚才还像工程兵一样勇猛的男医生瞬间变得婉约,心灵手巧地在我嘴里穿针引线。头顶的无影灯照射着他,他的剪影让我想起了从前在月光下做针线活的乡村妇女。风儿轻,月儿明,树叶儿遮窗棂。蛐蛐,叫铮铮,好比那琴弦声……我有点儿瞌睡了。
医生不让我睡,让我回家,边上还有个人咧着嘴等着呢。脸更木了,但耳朵的触觉无限放大,一粒耳屎在耳道里的晃动,像是在擂大鼓,奇痒难忍。用小拇指伸进去掏,脸肿得把耳道都压扁了,手指尖也伸不进去。
回到家里,我仿佛是功夫片里受了内伤的大侠,隔一段时间就吐出一口血水,说话气若游丝。媳妇儿看我的眼神有点害怕,说看你这样子,像是刚生了个孩子。
我的确感觉自己虚弱得像个产妇,而且一次生了俩。我仔细看那两颗牙了,骨头上还带着肉——那是我的骨肉。噢,孩子,妈妈不要你们了。
第二天,和年长我几岁的同事下乡,车上说起了他年轻时拔牙。那会儿麻药也不好,设备也不行,基本就是拿着钳子、锤子和起子生生往下撬,口腔搞得稀烂,两个多月才痊愈。听他说完,我立刻感觉自己的右脸不太疼了。
这两天你如果在街上见到一个人,一边腮帮子鼓胀着,嘴里像是含了一枚核桃,那可能就是我。向我行个注目礼吧,再过60年左右,看我就要收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