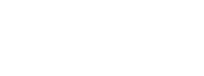季候风漫过麦田,父亲立在那里
口中呼啸着号子声,手中捋抚四方散去的麦香
脊梁上的晶莹让黄土地的醇更加浓厚,更加密实
这唯一辨认故乡的体味,成了我唯一的念想
一切都还在,小渠与沟壑与蚂蟥与水蛇
哗哗啦啦流淌的声音和扑哧扑哧攀爬的动作
在父亲的掌心使劲儿挣脱,父亲放入田野的小牛犊
尥起蹶子,一撒欢,就掠走了父亲的语言和呐喊
那段时光,父亲习惯了用爷爷遗传的旱烟袋
装上烟叶,就像母亲习惯了用外婆的针串起线
串起家。而我却在另一个季候风的漫延里
渐渐忘记了父亲口中呼啸的号子声和四方散去的麦香
以及那些消逝了的嘀嘀嗒嗒的省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