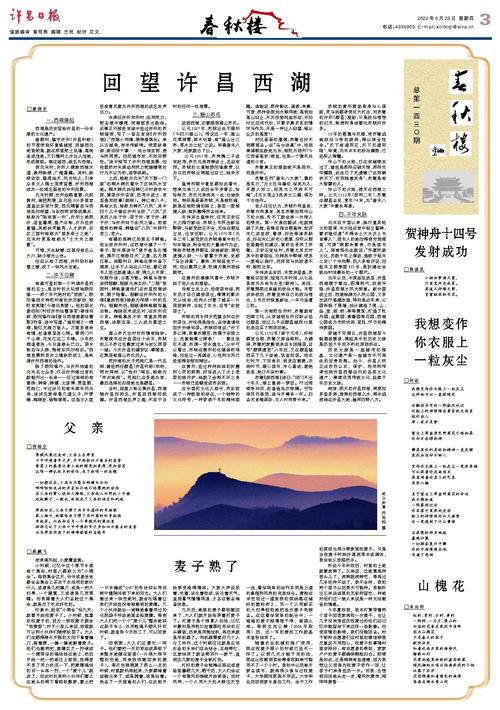夜来南风起,小麦覆垄黄。
小时候,记忆中这个季节乡里有个集会,村里人都称之为“小满会”。每到集会这天,爷爷或者爸爸都会去集会上买点干农活用的家伙什儿,或者是几把镰刀,或是一把大扫帚、一个簸箕,又或者是几顶草帽。而我跟着大人们去赶这个集会,就是为了吃点好吃的。
印象中,赶完“小满会”没几天,就要开始收麦子了。小时候,挺喜欢收麦子的,因为一到收麦子就会“放麦假”,对于小孩儿来说,放假就可以和小伙伴们随便玩耍了。大人们在晒得睁不开眼的太阳下拿着镰刀、弯着腰,一镰一镰地割着麦子。他们先割两把,麦穗交叉一拧做成一个腰带似的绳结放在地上,然后开始一把一把地往上面放,放得差不多了用力挤压一下,把麦穗绳结的另一头再一拧,一个“麦个儿”就成了。而此时的我和小伙伴们要么在地头的树下看蚂蚁搬家,要么把一只手握成“OK”的形状仰头寻找树叶缝隙间洒下来的阳光。大人们割出来一块空地时,就会吆喝着让我们开始捡没有被割到的麦穗。几个小伙伴就会一窝蜂地拿着用过的化肥袋子冲进地里去拾麦穗。等到大人们把一个个“麦个儿”整齐地码在架子车上,并用粗绳子捆扎好的时候,就宣告今天收工了,可以回家了。
回到家,大人们还要忙一阵子。他们要把一天的劳动成果卸下来整齐地摆在场里(一片很大很平整的空地,用来放收割回来的麦子)。等天色稍稍黑了那么一点的时候,村里就热闹起来,大家都端着饭碗出来了,或是蹲着,或是站着。洗去了一天疲惫的人们,在此刻开始享受难得清闲。大家大声说笑着,吃着,谈论着收成,谈论着天气,直到暑气慢慢消退,才各自散去准备休息。
几天后,地里的麦子都收割回来了,大人们就开始张罗着打麦子了。打麦子是个很累人的活,记忆中最初是用牲口拉着圆柱形状的石头碾场,后来是用拖拉机,再后来就是用机器了。用机器需要好几个人分工协作,这个时候往往就是左邻右舍的乡亲们自由结合,互相帮忙,这家结束了就去帮另外一家干,直到这几家的麦子全部打完。
打好的麦子会被摊在路边或者场里暴晒几天,晒干后,大人们会在一个有微风的傍晚开始扬场。找对风向,一个人用大大的木锨往天空一送,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是力道的拿捏和风向的完美结合。麦粒在半空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落在铺好的塑料布上,另一个人用新买的大扫帚轻轻地把些许麦子壳掠去。在这看似简单的配合中,一堆堆的麦子被清理干净,装袋入库。等到交完公粮(2006年取消)后,这一年的麦收工作就基本宣告结束了。
随着农业机械的推广使用,现在收麦子跟小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以前几天才能干完的活,现在从收割到卖给粮食收购商可能用不了一个小时。我初中以后离开家去读书,就再很少参与过收麦子,大学期间更是不用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参加工作,由于工作的原因也很少帮家里收麦子,只是当收麦子时刚好遇到周末或调休,我会给父母搭把手。
听说今年秋收后,村里的土地就要流转了。父亲说,这地算是种到头儿了,流转就流转吧,等再过几年他种不动了,我不会种,我的两个孩子以后更不可能种。我能听出父亲话语里的无奈和留恋,种地对他们这一辈人来说是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感。
今年夏收前,我本打算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再收一次麦子,也让几乎没亲身经历收麦过的他们在记忆中能留存下来这样一些影像。但受疫情的影响,我们没能回去。村干部和志愿者们在村里的微信群里反复说不用担心,收麦子的事情村里安排好,有志愿者的帮助,家家户户的麦子都确保颗粒归仓。即便是如此,还是稍稍有些遗憾,因为我想让父母再为收麦子劳作一回,让孩子们亲身经历一次。而我,也想到田间地头走一走,看风吹麦浪,闻阵阵麦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