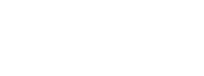乡下娱乐,有两件事让人耳热心跳,难以拒挡——“逮鱼撵兔,神仙见了不挪步”,“鱼线一响,不当县长”。后一种说法确有出处:相传庄子爱鱼,钓于濮水,楚王派大臣请他做官,庄子仍持竿而不顾。其实,同为热闹事,它们的侧重点却迥乎不同。捉兔,人吆犬吠,兔在明处,为生死蹿。仔兔掌大,老兔尺盈,悬念在于捉到与否和兔死谁手。为渔,鱼潜水底,人在岸上,明暗倒置,想象空间被无限放大。苇漂沉浮,纤丝颤响,永远不知道下一条是何鱼,有多大。
这很容易让人上瘾,入梦。
何况,村后,河的北岸,有个存世多年,从没有干涸过的大坑。
一
这是条自然河,也是古河道。它遇村傍村,顺势连上村寨的沟渠水塘,多数时候,就在田间地头散漫游走。水大行洪,旱季灌溉;春来百草萌芽,夏至柳影绿荫,秋后水清沙白,冬天,冻实的浅滩,是村里的溜冰场。沿河乡民默认了它的野性,很少围堵疏挖。河呢,遇到软地就多掏几把,施展施展拳脚;碰到硬胶泥砂礓石,立刻缩手退避,收成一条小泥沟,匆匆穿过。大家不知它源于何处,也不知它流向哪里。一路走过,散落一串串青丝丝、水凌凌的段落:沙坑,窑坑,苇子坑;岗上,闸下,排水渠;柳树林,莲菜地,鲤鱼沟……
杨树坑是这里为数不多的大坑。它在河北岸,岸上是高岗,土质细柔肥实,旱了随手浇,涝了就地排,种啥成啥,是难得的高产田。这个地方,先人不能任由野河撒欢儿,沿河岸栽上齐刷刷的毛白杨。河水冲刷依旧,杨树年年生长,前排倒下,后排顶上,杨林成材的时候,堤、坡、树、水达成和解,杨树坑变成大大的回水弯,终于消停下来。
大坑的水下却不平静。沙石河底,汛流冲刷,乡民常年捞沙,水底早已状况难辨。几年不汛,泥沙淤积,大坑深处不过丈余,大水过后,则又潭窝遍布,河底泉眼,犹如桶粗。相传有年大汛,河水进了杨树坑,立刻被潭窝吸住,满坑的漩涡,大如磨盘,小如锅盖,时而套合,时而拆分,变幻莫测。
有村妇在南岸洗涮,对岸明明无人,却有异响,定睛细看,一条大蛇正匍匐于地,蛇头上扬,吃力上爬。头及树杈,尾还在树下,上半身失重,坠下,声若粮袋扑地。有年炎夏,一老汉岗上耕作,暑热难忍,见树下岸边卧有青石,遂圈腿坐上,抽烟歇息。烟毕,顺手在石上磕烟灰,一敲,两敲,三敲刚抬手,青石竟缓缓移动。哪是飞来石?原来为鏊大老鳖一枚。
在乡下,蛇鳖历来有故事,大家宁信其有,宁信其大。杨树坑的鱼却是那个年代村人实实在在的口福之物,由于大坑的天然庇护,如仓中之粮,唾手可得。每年后秋水位降下来,生产队都要组织社员下河捕鱼,这是全村的盛事。抬网抬,围网围,粘网挂,撒网盖,或闸堰筑坝,拦下一段,机抽瓢舀,竭泽而渔,尺长的鲤鱼草鱼鲶鱼黑鱼,黄辣丁大白条,螺蟹鳖鳅,男劳力忙活一晌午,家家都能分得半桶一盆。有种鱼叫噘嘴鲢,形似白条,却是吃鱼之鱼,本为大水面之物,在杨树坑竟也长到三尺。水中还生有红鲤鱼,群戏孤游,就在水面漂着,动静大了才缓缓下沉,一转眼,换个地方,从绿水青草中升了出来。
见到杨树坑真正的大鱼的,是我的伯父。他是生产队会计,经常到大队对账。有天凌晨路过大坑,突传巨响,如人落水扑腾,朦胧月色之下,一大鱼在浅滩戏水,宽若门扇,身长如人。伯父说,惊吓之间,他已分不清鱼种,这样大的鱼,实属此生第一次见到。此后不久,为逼大鱼出水,村里年轻人做成土炸弹,轰遍杨树坑,白花花的鱼捞了几背篓,大鱼却始终不见踪影。第二年春上,又有人弄来“鱼塘清”,半月之后,还有鱼在水里晕游,大鱼仍未现身。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给城市修饮水渠,老河道被冲,浅处挖,深处填,荡平了杨树坑。已是深冬,坑底的蛤蟆挖了几大筐,还是没有见到大鱼。
伯父当会计多年,精打细算出名,言语从不夸张。杨树坑真有“大鱼”吗?大家有了疑问和争论。时光如水,大鱼、大蛇、老鳖,早已化作大坑的神物,留在了村人的追忆里,无人考究其真实与否。
二
河里最多的鱼,是 “河著”——鲫鱼。
此鱼不知避害,喜集群,反应又奇慢,有鱼谚云:“鲫鱼片儿,跑不远儿。”它的长处是适应能力强,食性杂适,当年出生,当年甩子繁衍。长得不大但量多,生长缓慢却常年开口儿,这样的特性确定了鲫鱼是渔事尤其是野钓的首选对象鱼。二三两已是板鲫,半斤为大惊喜,斤鲫堪为奇迹,运气不佳者,钓一辈子鱼,终生不见。我自幼嗜水,钓历始发杨树坑,野钓作为消遣,成为业余“铁好”,已二十载。由于粗针大麻线的秉性,钓技始终处于中下。纯属运气,2014年寒冬,我经历了一个神奇大鲫之夜,至今念念不忘,却又百思难解。
那年冬至时节,本地钓界盛传南阳鸭河口水库出大鲫,半斤四两是主力,时有斤鲫上岸。一个雨雪交加的午后,驱车三小时赶到,选定钓位, 装配线组,和饵打窝。酒足饭饱,雪还在扑扑下,夜色灰白,竟生出些微暖意,感觉今晚有戏。
果然,晚9时进入爆连模式。如镜的水面上,夜光漂稳稳点进或高升半目,抬竿均是木木的手感,出水便是闪着银光的板鲫。两小时过后,鱼口变缓,上来的鱼却增大了两号,条条要用网抄,目测大多过斤。午夜过后,漂相越来越轻,有的时候全凭感觉,发丝之变,抬竿即中,鱼更是越钓越大,坐着控制不住,条条都要站起来遛,中间上了几条鲤鱼拐儿,三斤左右,感觉后期所上鲫鱼,已与其不相上下。临近黎明,人困马乏,夜光漂又稳稳下沉,决定以此鱼收杆,不想它竟不慌不忙要起线来,判断是条鲤鱼。几个回合下来,胡乱收进抄网,分量沉重,应该是当晚最大之鱼。
第二天,雪霁云开,期待再续辉煌,结果大出意外,直到中午,浮漂如进水缸。鱼获出水,大吃一惊,最大一条竟是鲫鱼,鱼身肥厚,四向外扩膨胀,呈浑圆形,弹簧秤一拉,指针过了五斤。当地钓友惊叹连连,久闻库里有十斤鲫王,几十年来,网捕鹰叨,从未谋面。钓到如此硕鲫,已属本库多年鲜见。何时钓上的?脑海中迅速复盘,应是最后上的那条“鲤鱼”。
以后几天,鸭河口水库钓友趋之若鹜,多失望而归,上大鲫者更是寥寥。以后几年,逢冬雪之夜,我必赴鸭河口,天气水温等同,心志满满,却一次次“空军白皮”。
我时常恍惚,鸭河口之遇不是梦吧?
一夜之间,老鲫们去哪儿了?
三
我野钓大鱼的记录,是信阳南湾水库的草鱼;最大跑鱼记录,也是在南湾水库,一条巨青。那是在同一钓位,用的同一套钓具,时间相隔半个月,钓到的在傍晚,跑掉的在黎明。
因为对象是大物,自然有备而来。手海两用竿,前打轮,带卸力,有刹车;8号通线,单钩,连抄网也换成了巨物抄。此处是老钓点,对周围环境了如指掌——左手为沙底浅滩,水深3米,右手是一小山包,坡岸立陡,周围树根盘错,极易挂线跑鱼。钓的那条大草,似有先判之明,一头扎向右侧小山包,多次遇险,屡屡惊变,博弈一小时,终于翻白上岸,净重25斤。跑的那条,感觉一开始就有些异样,舍右奔左,势大力沉,闷头要线,一口气冲出几十米。惊心动魄之余,暗喜,此处水底平坦,无挂底之虞,如向右冲出这么远,一旦回头,如此力道,必然钻向树根。左边是开阔地,线轮脆响,波澜不惊,出线收线,反复循环。不觉之间,一个半小时过去,天大亮,鱼已在十米之内,浮上了水面,大口喘气。它青白泛光,身长米半,头如斗大,是条乌青,目测比钓到的草鱼大过一圈,应在50斤以上。按下狂喜,定定神,准备决战,却倏然吓出一身汗:鱼翻肚处,正是水位下落时泊船之处,水面之下,立有木桩。惶恐之间,大青似有灵犀,突然下沉,胡乱起竿,鱼线已轻如鸿毛,只见蒲扇大尾,船桨一样缓缓挥动,悠然远去……
情绪稳定,我慢慢明白过来,这条鱼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右逃。难道它知道,左边水下有根木桩?
商城鲶鱼山水库,水好鱼大,当地人不食鲤,是远近闻名的大物圣地。因为资源丰富,频出达人、大师。有周姓老师,鱼钓得好,也写一手好文章,常在钓鱼杂志上发表,我久慕其名,几年前终于库畔相见。周老师钓大鱼无数, “秘方”却大道至简。大师说,钓大鱼首先要诱到鱼,要提前几天打窝、补窝、养窝,要静心苦等。他从不用花花绿绿的商品饵,坚拒小药。他的经验,鱼越大越谨慎,它们在暗处,始终在观察,安全了,才一点点靠近。对周围环境,鱼比人清楚。大鱼上钩,更大的鱼一定在远处察看;最大的鱼,人永远钓不到。
周老师讲道理的时候,眼没有离开过水,黝黑的面庞,始终静若止水。经历多年江湖风雨,他说,他还没有真正认识鱼。
他的一席话,把我带回鸭河口水库、南湾湖,带回了杨树坑。我终于相信,伯父的“大鱼”,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