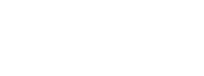李俊涛
第三天早晨,年轻女子又一次清醒的时候跟父母说:“让俺哥来吧。”
上午十点多,老人的大儿子过来了。他跟我年纪差不多,在建筑行业做项目经理,脸晒得黑红,头发已经花白了。他比妹妹大十多岁,说妹妹从小是他抱大的。他让父母回去休息,打湿了毛巾轻轻地给妹妹擦脸,用纸巾把妹妹凸起的牙齿一点点擦得很干净。他这么做的时候,一直保持着微笑,无限柔情地看着病床上的妹妹,仿佛她还是从前那个总喜欢缠着他的小姑娘。
年轻女子说:“哥,我快要死了。”他说:“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呢。”
年轻女子睡着的时候,他跟我说:“唉,这两年我净是办这些事儿。办了老二的事,父母还没缓过来呢,现在又要办妹妹的事了。妹妹的事办完,我准备带两个老人去旅游、散散心。老家我是不让他们回去了,让他们跟着我。我有两个孩子,看着孙子、孙女,他俩才会把我弟弟、妹妹忘一会儿。”
老汉说过,女儿看病的钱大部分是大儿子出的,女儿的房卖了,能填补医疗费的空缺,剩下的也就那辆车了。
老汉的大儿子中午没吃饭,一直静静地看着病床上的妹妹。妹妹偶尔醒来时,他就笑着和她说话。人不是到了中年就有了中年的状态,中年的沉稳平静是生活打磨出来的,当生命中不断有东西无法挽回地失去,我们就渐渐有了一张波澜不惊的脸。
黄昏时分,年轻女子陷入昏迷中再也没醒过来。她“啊”的一声,吃力地往外吐一口气。那声音在病房里碰撞回荡。她哥哥跟医生交流后,给她买回了寿衣。
我问母亲怕不怕,要不然找护士给我们调个床。母亲说:“不怕,怕啥呀。”我也一点儿不怕。母亲患病7年了,我们共同闯过了好几次鬼门关,心在生死线上煎熬过几次,经历过极度的绝望和崩溃,真的是什么也不怕了。
死亡有时是一瞬间的,有时却是艰难漫长的。年轻女子的吐气声持续了一夜。母亲睡着之后,我在她身边的行军床上也躺下了。母亲说我睡得很香,鼾声如雷。
第四天早上,年轻女子的吐气声仍在持续,只是微弱了许多。老汉和老太太来了,老两口儿知道最后告别的时刻到了。老汉不说话,一直默默地流泪,老太太捧着女儿的脸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妞,你真不要妈了,你真不要妈了……”年轻女子的哥哥劝老汉陪着老太太回家。
年轻女子在下午四点多钟停止了呼吸。当时,她哥哥靠墙坐着,疲惫得睡着了。我忽然感觉空气中少了点儿什么,过了片刻才发现年轻女子没了动静,过去叫醒了她哥哥。他去叫医生,我看见年轻女子的脸变得平静舒展,所有的痛苦和焦灼都逝去了。不过,她的眼睛睁着,只是眼球没了黑白,变成了灰蒙蒙一片。
医生过来了,测了年轻女子的心跳和脉搏,然后记下了一个时间。护士来了,拔掉了年轻女子身上所有的管子,她昏迷时多次想要拔掉这些管子,家人只好绑住了她的双手。现在,她终于自由了。
年轻女子的哥哥迅速给她换上了寿衣。她没有穿上想穿的白裙子,中原地区的丧葬礼仪不允许。哥哥一边换衣服一边对她说:“妹妹,白裙子我烧给你。”那套寿衣里外共五件,最外边的是桃红色的唐装,花团锦簇。我曾想过过年时做一套唐装穿,现在打消了这个念头。最近见到的几个逝者,都是穿着唐装。哥哥抹上了妹妹的眼睛,用一块儿纱巾蒙上了她的脸。这个中年汉子再也忍不住了,扭过脸抽泣起来。从此以后,妹妹将只存在于他的回忆之中,兄妹三人只剩下他一个了。
殡仪馆的车很快就来了,哥哥抱着妹妹把她放进了那个锦缎装饰的长盒子里。他又回来跟我和母亲告别,向我们表示感谢,说给我们添麻烦了。他让护士通知清洁工清理病房里的物品,说所有的东西都不要了。他前一天跟我说过卖了妹妹的房子,这座城市可能永远都不会再来了。我跟他说:“节哀,照顾好两个老人。”
清洁工迅速把年轻女子的遗留物品清了出去,擦了桌子拖了地。护士给那张病床换了一套新床单、被褥,洁白平展。
第五天上午,一个新的病人搬了进来。之前护士跟我和母亲交代,不要跟新搬进来的病人说这张床上刚死了人。我们说:“放心吧,不说。”
其实,说不说大家也清楚,肿瘤病房的哪张病床上没死过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