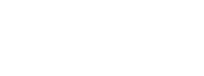记不清哪一年了,在老家许昌,与同学朋友盘桓。我的酒量不济事,三杯两盏之后,天旋地转之中,被裹挟着拜见了常德生先生。
那时候他刚以某局局长致仕,中国人的习惯,以官为贵,皆称“常局”,现在也仍然。局座府邸,与寻常百姓家无二,甚至更寒素一些。室内则像考古队的工棚,又像是打拓片的作坊,砖瓦碑志、笔墨纸砚、毡刷碗碟、书画卷轴一应物什,像是弄乱了正归置,又像是归置了又弄乱。同行五六人,各自开辟了坐处,或烟或茶,或说碑帖,或谈诗文,或插科打诨,一室淆乱。踱到阳台上,则陶瓷金石,汉魏明清,密密麻麻……怎么告的别,没有记忆。
常德生先生生于1953年,肖蛇,大我一轮。瘦高个儿,多年的衙署生活,没有怎么改变他阳光下的肤色,眼光里则有执着、有狡黠、有深情、有自负,说话轻松,但说到动情处,会不自觉地加快语速、提高调门。大抵“文革”后最早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一批人,十之八九,有才华、有毅力、有勇气,该经历的都经历过,想做的事会矢志不渝。他年轻时是“文青”,写小说,写散文,后来发表一些,也就成了所谓“作家”。作家不作家倒无所谓,更潜在的,有一颗向慕文化、崇尚风雅的诚心。
就像初恋情人永远忘不了一样,有些情结,根植于灵台,夙志不申,想做的事不弄出个样儿,就不能长舒一口气。常德生先生是作家,但恕我直言,不算著名,这有两个原因:其一,他由教育到政法到人社,阅历丰富,但恪尽职守,也会陷于事务,就是我们常说的“日理万机”;其二,不知道什么时候,兴趣转向金石碑版,越来越上瘾,一发而不可收,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能自拔”。世上有两种人,一种城府深,干活不会累,喝酒不会醉,凡事分寸拿捏得刚刚好;一种纵情率性,做事全力以赴,诗能下酒,剑可赠人,轰轰烈烈,就图个痛快。常德生先生属于后者。既然喜欢,也就一往情深,听说哪儿有名碑大碣,有断砖残石,公余之暇,欣然规往,手自椎拓。或拓,或买,或换,春去秋来,不知老之将至。钱花了,罪受了,而隔三岔五有所获,宛如抱得美人归,摩挲呵护,快感荡漾,胜却南面为王,此乐何极!人生百年,天道无私,有所失必有所得,有所苦必有所乐,若三餐一睡,平铺直叙,数够年头交账,也可能算是生而无为;然而想有点儿动静、有点儿振幅、有点儿刺激,就要折腾起来,歌哭笑傲,才不枉这一轮回。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此之谓乎?
治金石之学,整天沉浸于阴幽湿冷、乌漆麻黑之中,有何意思?大抵可发思古之幽情,逝者如斯,令人依依;可补文献之不足,知前人所未知;可得见所未见的惊喜,在无可名状的形式感中,收获愉悦和启迪。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学识,转移了性情,此中甘苦,不足为外人道也。
然而,学术艺术毕竟要传播,要向外人道。2013年,常德生先生在许昌学院举办展览时,张宏伟先生还在那里做教授,我们一道享受了饕餮盛宴。学书法的人都知道,看印本不如看拓本,看剪贴本不如看整拓,看整拓不如看原石。原石在天南海北,整拓又尺幅巨大,如果能把这些拓片集中出版,“想来也是极好的”。常德生先生倒并不在意雁过留声,但这样建议的人多了,也便动了心,个中前前后后,他在《后记》里说得很清楚,我就不重复了。
金石之学,不论如何发达,其核心知识,大抵在于古人题跋中。常德生先生从事收藏,当然也不止步于“据为己有”,而是研究、考证、评论,必知其然而后可。所作笔记,也足可雁行古人。然而筹划出版,则又发愿征集百位书家题跋,于是又有几年折腾。书家分散于五湖四海,有牛气哄哄者,有文质彬彬者,有学养深厚援笔立就者,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者,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常德生以人格魅力、人脉关系、学识阅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醉之以酒,使之以钱,终于,“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这里的书家题跋,略可为当代书坛创作风格缩影;拓片与题跋文字对读,书家之学力,亦暴露无遗。请索过程中,酸甜苦辣,在常德生心中,自成众生活剧,他年有暇,写成一部“书林外史”,亦未可知。
书就要付梓了,总名《汉风遗韵——百位名家题跋两汉精拓荟萃》,分《汉碑》两卷、《汉画像砖》两卷、《汉画像石》一卷、《汉瓦当文字砖》一卷。除百位书家题跋外,每拓均有常德生题识,并收其考察报告、考订辨析、艺术鉴赏类论文,堪称煌煌巨著。
半辈子心血,做这一件事,所为何来?好像也于事无补。但吾许旧邦,尤以汉魏辉煌,寻常巷陌,可能发生过惊天动地的事;一抔黄土,可能埋葬过震古烁今的人;三字残石,可能牵涉重要史实;一片砖瓦,可能演绎着先民的故事。而汉魏旧都,文物衣冠,虽岿然自在,今天的人,真要实实在在地了解,也不容易。有了这部书,以后我们就会说,我们许昌有个金石家常德生,深研汉魏。他怎么深研了?他有一部《汉风遗韵——百位名家题跋两汉精拓荟萃》。
(本文原载《汉风遗韵——百位名家题跋两汉精拓荟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