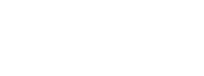我和奶奶坐在院子里。
小黑狗卧在脚边,几只母鸡咕咕叫着来回走动,石榴树、葡萄藤、两株凤仙花,都静默不语。
玉米秆正烧着火苗舔着黑黑的锅底,火焰会发出啪啪的声音,冒出缕缕烟雾来。那燃烧的味道直钻进鼻子里,又分成丝丝缕缕,遍布全身。整个人就在这有点儿甜、有点儿焦的味道里沉静下去。
奶奶要给我煮鸡蛋吃。我烧火,奶奶拿鸡蛋。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这是下午三点的秋日阳光,明亮温暖。
鸡蛋煮好了,捞出来放凉。
祖孙俩就在阳光里坐着,并不怎么说话。
阳光有令时光静止的魔力。似乎坐了好久好久,蓦一抬头,太阳依然又大又光芒万丈。天空湛蓝,远远一朵白云,新出土的一望无际的麦田,都给它做了最和谐的背景。这一切融合在一起,散发出一种清新温暖的泥土的芬芳。
秋风卷着树上和地上的叶子,飒飒作响,像经典电影里的背景音乐一样低回沉寂。
我说,奶奶,给你剪剪指甲吧?
奶奶像孩子一样,乖乖伸出手来。这一双手粗糙又纹路横生,指甲缝里都是泥土。我认真剪着,奶奶望着我,安安静静。
想起小时候,常常把小脑袋放在奶奶膝盖上,奶奶用她粗糙的手摩挲我的头发和脸,我猫一样趴着不动,享受人间最宠溺的爱抚。
现在也想趴在奶奶膝上,可是奶奶越来越老、越来越小。
我坐在她身边,愈发显出她的瘦小,奶奶已经百岁有余,她是真的老了。
奶奶平氏,无大名,小名大妞。生于哪一年不知,身份证上写着1914年。
奶奶从不谈往事,不知是真忘了还是不愿回忆。只从父辈零星的描述里,知道奶奶嫁给爷爷后,我太奶奶对她不好。
奶奶一生养育五男二女,为了活命,讨饭、流浪、辛苦劳动……
我是奶奶的大孙女,出生没多久,就跟奶奶睡,直到上初中。
半夜饿了,做了一天农活的奶奶起来给我擀面条吃。
半夜不想睡,就一定要奶奶抱着我到家隔壁学校操场悠悠。
长大后不知是邻居们说多了,还是我确实有模糊记忆,好像真就记得在夜里,奶奶迈着小脚,抱着胖乎乎的孙女走在操场上,孙女看着清亮的月亮,再迷迷糊糊睡去。
我却清楚地记得冬日清晨,奶奶把我抱在怀里,用手焐热了棉衣棉裤再给我穿上。
记得奶奶把我放在厨房炉火旁,给我烤红薯吃。
记得奶奶一把一把给我剥瓜子仁吃,我总是一口吞掉。
记得我笑着跑着扑到奶奶怀里,碰掉了奶奶一颗牙……
童年记忆里都是奶奶,都是奶奶的怀抱。那时的我,觉得全世界都像奶奶的怀抱一样踏实温暖。
当然记忆里也有奶奶的哭声:子女众多,家境贫寒,一次次分家,一次次吵闹,锱铢必较……
爷爷在我没出生就瘫痪了,是奶奶一个人伺候。稍不如意,爷爷就对奶奶发脾气。我气不过,故意惹爷爷生气,爷爷拿棍打我,我一边跑一边说,你打我呀你打不住。奶奶看见了,就把我拉走,说不能惹爷爷生气。
奶奶从没有打骂过我,一句重话都不舍得说。
长大了,外地上学第一个月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找奶奶。奶奶一见我就哭,我也哭,祖孙俩并不说话,一任眼泪恣肆。
毕业上班直到前年,这二十多年,除了每个月回家看奶奶外,我没想过好好陪伴她老人家。
奶奶每次都说,你忙你的,我好得很。
我真以为她好得很。自己做饭、洗衣服,走路不用拐杖,上房顶摊晒玉米、小麦,给我纳鞋底,用玉米皮搓绳子卖钱……
我给她买各种我以为她需要的东西,从不吝啬。
我以为这就够了。
我甚至不记得,这二十多年,奶奶是怎么一点点越来越老的。
直到前年,奶奶不会做饭了,奶奶开始用拐杖了,奶奶走几步路就走不动了。
我开始慌了,我害怕起来……
我一次一次回家,一看见奶奶就心安。
指甲剪好了。剥鸡蛋吃。
我把鸡蛋给奶奶放嘴里,奶奶看着我,像当年我依偎着她的眼神。
奶奶边吃边说,孙女,我就是个废物了吧?活着啥用啊?
我说,不是奶奶,您不是!我回来了叫奶奶有人答应我啊。
如果说这世上我还有财富的话,那就是奶奶给予我的,无穷无尽犹如滔滔江水一样的爱吧。
这是我在尘世被戏弄、历尽劫难却始终带着纯真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变得刀枪不入、玩世不恭的根源所在。
时常惊叹奶奶顽强坚韧、旺盛蓬勃的生命力,一百多年,对一个人,特别是一生经历那么多苦难的女人来说,何其漫长,奶奶是怎么一点点、一天天、一年年熬过来的?
也许,悲苦原本就是生命的底色。唯其,方能珍惜为数不多的欢愉吧?
阳光有情,时光缓慢,我和奶奶坐在院子里,我们互相打量,我们彼此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