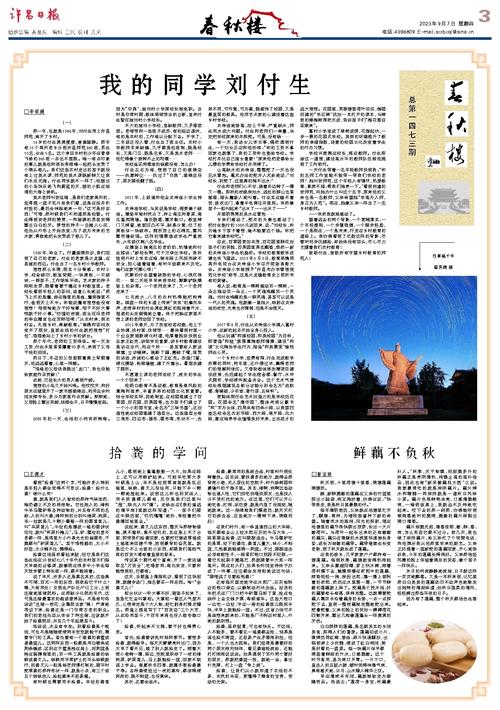看到“拾粪”这两个字,可能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拾粪?拾什么粪?做什么用?
粪,就是我们人人皆知的那种气味浓烈、唯恐避之不及的排泄物。它包括人的、猪狗牛羊马骡驴等各种动物的,并且有不同的名称:人的叫大粪;猪和狗的分别叫猪屎、狗屎;羊一拉就是几十颗小葡萄一样的圆蛋蛋儿,叫“羊屎蛋儿”;牛拉的是摞成一堆的圆饼状坨坨,就叫“吽屎扑摊儿”;马、驴、骡拉的差不多都一样,是鸡蛋大小外表光光的扁圆形,干脆都叫“驴屎蛋儿”。至于鸡鸭鹅的,太小不好捡,太少搁不住,懒得拾。
拾粪这活虽然看起来脏,但它是我们这些生活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孩子们每天早晚的必修课,就像现在很多中小学生每天放学要上特长班一样,都不能闲着。
说了半天,许多人还是莫名其妙,这些臭不可闻、百无一用的东西,到底拾它干什么?嘿,大有用处!交到生产队论斤记工分,上到庄稼地里做肥料。在那缺少化肥的年代,这可是庄稼最喜欢的超级营养品。不是有句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嘛!严肃地考证下来,拾粪还是一门非常古老的职业。我们的老祖先自从学会了种庄稼,应该就开始了拾粪肥田,并且几千年延续至今。
俗话说,术业有专攻。别看拾粪是个粗活,可也不是随随便便两手空空就能干的,需要专门的工具。首先要有一个装粪的粪筐或者粪篮儿。这两样东西一般都是用白蜡条或荆条编成,区别在于筐是挎在肩上,而荆篮是挎在胳膊弯里的;另一件工具就是拾粪的铁锨或粪叉儿。铁锨用平常铲土的平头铁锨就行,而粪叉儿一般是铁匠师傅打制的,跟平时挖草粪的那种形状一样,就是小点,有三个或五个细铁齿儿,拾起粪来不容易漏。
有时候也需要用手拾粪。羊拉的粪蛋儿小,落到地上蓬蓬撒撒一大片,如果在路上,还可以用锨铲起来。可赶羊吃草大多时候是上山,羊不是拉到草窝里就是乱石堆里,铁锨、粪叉儿没法用,只能下手一颗一颗地捏起来。说到这儿你也别笑话人,用手抓粪哪儿都有,无非是我们这里叫“捏”,陕北人叫“撮”。史铁生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里就这样写道:“……孩子们跟在牛群后面,‘叽叽嘎嘎’地吵,争抢着把牛粪撮回窑里去。”
说起来,粪叉儿这东西,整天与那秽物接触,黑不溜秋、臭不拉叽的,实在是上不了台面,即使我们拾粪回家,也要把它插进草堆或土堆里来回搓干净,放到最背的旮旯里。就是这个不上台面的小东西,却跟我们高档气派的百货大楼有着直接的联系。
传说某个朝代有个富商,开了一家店铺取名“万货全”,吃喝穿用、南北京货,只要你能想到的,它都有。
这天,当朝皇上微服私访,看到了这块招牌,就踱步进门,指名要买一样东西。啥?“金粪叉儿!”
柜台伙计一听大事不好,砸场子的来了,急急忙忙去叫掌柜。大掌柜一看这人气度不凡,心想肯定是个大人物,赶忙躬身打揖求赐名。那皇上提笔写下了“百货店”三个大字,从此沿用至今,千百年来再也没人敢夸海口了!
拾粪,听起来不文雅,要干好也得费心思。
首先,拾粪要讲究时辰和季节。要想多拾粪,就得趁早。每天天蒙蒙亮时出门,因为太早了看不见,晚了别人就拾走了。顺着大街小巷转一圈,路边、空院里积存了一夜的猪狗屎、驴屎蛋儿,马上就能拾一篮,回家不耽误上学去。春夏秋冬四季,就属冬季拾粪最干净。各种粪便经过一夜的寒冷,都冻得硬邦邦的,既不粘篮,也没臭味。
其次,还要会战术。
拾粪,最常用的是游击战,村里村外到处转着找。说实话,要找粪多的地方,就得去那背街小巷、无人居住的空院子、村外杨树园和寨墙外的干海子里。其实,猪啊、狗啊这些动物也通人性,它们找吃找喝找朋友,也是找人少不受打扰的地方。在这里,它们可以开心地吃食、打闹、谈恋爱,就是内急了没规矩,随地就来。这一规律被我们摸透后,就天天打它的游击战,这些地方一圈转下来,满载而归!
在我们村外,有一条直通西山的大车路,每天都有去山上拉水泥石灰的牛马大车,一路紧跟去拾粪,这叫跟踪追击。牛马骡驴吃的是草,拉下的粪坨、粪蛋儿量大、味小、不粘篮,几泡粪就能装满一荆篮。不过,跟踪追击必须有耐性子,一路紧盯牲口屁股不眨眼,一看它扎起架子翘尾巴,那就跟要中大奖一样高兴。现在的人们,如果长时间坚持终于办成了一件事,往往都会发泄般地说这句话:“跟哩远了总要拾泡粪!”
还有每天固定地守在水泥厂、石灰窑附近的牲口旁边,以静制动打伏击战。拉货的车把式在厂门口把牛驴骡马卸了套,拴在电线杆上去交钱开票,等候装车。这些大牲口一边吃一边拉,守在一旁的拾粪孩儿眼疾手快,半早上就能拾一篮。不过,这省力活可不是谁想来就来的,只能是厂子附近村里人,外地的就别想。
拾粪,虽然脏累,可也有快乐。干这活,人不能多,要不看见一堆粪都去抢,结果是谁也拾不满篮,还容易产生矛盾闹别扭;但是,一个人也太孤单。我们经常是最要好的两个朋友相约结伴,看见粪堆轮流拾,还能打打闹闹说说话。如果遇到了另外两个要好的朋友,那就把粪篮一放,就地一坐,拿出扑克牌,打上一盘“争上游”。
拾粪,让我们从小就知道了农活的不易、农民的辛苦,更懂得了粮食的宝贵、劳动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