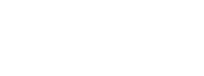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知道老师的呢?我循着记忆的桨,努力地在岁月的星河里漫溯。
6岁那年的9月,父亲把我送到村幼儿园,我拽着父亲的衣角怯生生地跟在他的身后。“看着虎头虎脑的,真可爱。”一个长辫子老师拉着我的手,边说边把我带到了教室。我在小伙伴们中间胆小是出了名的,教室里端端正正坐着的几个小伙伴望着我露出了促狭的笑容。
那时的幼儿园没有固定校舍,经常变换地点,今天在村部,明天可能就在牛屋。我们最兴奋的就是下午放学时老师突然宣布明天换了地点上课。有一次在村中几间闲置的老房子里上课,闲置的房子倒没有什么,让我心悸的是教室旁边的空房子里有两副棺材,每次经过那儿我都是战战兢兢,生怕棺材里会跑出什么来。
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天早晨我去得早,当我小跑路过那间放棺材的房子时,几个小伙伴突然张牙舞爪地冲出来,吓得我哇哇大哭。“老师,老师……”我声嘶力竭地喊着,好在长辫子老师正好赶到学校。她把我抱在怀里轻声地安慰着我,抽泣中我竟然在老师怀里睡着了。睡梦中,我感觉老师怀里好安全,好温暖。
我的手指短粗,手背肉多,手握起来掌指关节处都是平的。每到天寒地冻的时候,我的手就肿得像一个笑开嘴的大馒头,连笔都握不住,经常会从裂开的口子里洇出血来。为了治疗我手上的冻疮,父亲想了好多方法,辣椒根和茄子根熬水浸泡,各种冻疮膏涂抹,要不是我反抗,连抹活麻雀脑都要去尝试。经过一番折腾,我的手没有丝毫好转,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上小学时,有一次考试,冻疮流血染了试卷,胡老师发现了把我喊到教室仔仔细细地检查了我的手,在盆里倒了热水,用镊子夹着棉花细细地把我的手擦拭干净,然后用碘酒消毒,最后涂上药膏。涂药膏的时候,胡老师用手轻轻地给我按摩,温暖的感觉从胡老师的手上传遍我的全身。胡老师还特别叮嘱我,以后每天到他那儿给我涂一次药。半个多月后,我的手竟奇迹般地好转起来。现在每一次摩挲着曾经裂口的手背,我就会想起胡老师,他在我童年的天空里涂抹了一大片亮色,给了我满满的一个温暖的冬天。
读大学时,家里经济入不敷出,父亲东借西凑好不容易给我交了1万多元的学费,我在学校读书时的经济条件可想而知。班主任尚老师给我争取了500元的资助款,资助仪式那天每人还发了一条棉被。虽然钱不多,但是足够我3个月的生活费;棉被不是很厚,但全新的棉被盖着非常温暖。那几年的冬天,感觉被窝总是热乎乎的。
毕业后,这条棉被我一直用着,后来还被作为儿子的襁褓。每每看到这条棉被,我的心里总是暖暖的,我永远记着尚老师当时说的话:“生活贫穷一些只是暂时的,我们要做一个精神富有的人。”至今,尚老师的话犹在耳畔,温暖着我一路前行。
如今,大学毕业已经做了20余年的老师,我也曾在冬天脱下棉手套给学生暖手,掏钱给孤儿学生做急性阑尾炎手术,号召全校老师给家庭贫困的学生捐款捐物……我也在努力做一个学生们心目中温暖的人。